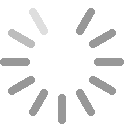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75302968
-
书名
在遗忘之前告别
-
作者
[美] 埃米·布卢姆 著
-
出版社名称
译林出版社
-
定价
68.00
-
开本
32开
-
译者
俞敏 译
-
出版时间
2024-11-01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众望所归的年度力作,横扫2022年各大榜单。《纽约时报书评》《时代》 NPR 《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今日美国》《科克斯评论》《展望》《出版人周刊》《每周娱乐》 美国亚马逊 《星期日泰晤士报》 一致推举的2022年度图书。
备受瞩目的天赋作家,被誉为“美国当代雨果”“当代美国最为独特、最有天赋的文学声音之一”。阿兰·德波顿、厄休拉·勒古恩、迈克尔·坎宁安、科伦·麦凯恩、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谭恩美齐声赞誉。
读者票选的口碑之书,真实、震撼、感动。《纽约时报》畅销书,美亚2022年度回忆录,Goodreads两万+读者打分的年度回忆录提名。
内容简介
她是作家、“美国当代雨果”,也是一个帮助阿尔茨海默病丈夫寻求安乐死的女人。
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安乐死,从失忆失智失能的生活到体面的离去,一个人要跨越多少医疗、法律和伦理的难关,一个家庭要经历多少次抉择、哭泣和告别?
以凝练之笔,埃米·布卢姆记录这段鲜有人走过的路途,讲述她如何竭尽全力为丈夫寻找无痛、合法、有尊严的生命终结方式,并最终在瑞士实现他的愿望。书写爱与失去,也书写生死沉思,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回忆录。
作者简介
埃米·布卢姆(Amy Bloom),生于1953年,美国小说家、编剧、精神治疗师,被誉为“美国当代雨果”“当代美国最为独特、最有天赋的文学声音之一”。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现执教于维思大学,教授创意写作。
另著有长篇小说《白色房子》《幸运的我们》《远离》等,短篇小说集《请来找我》《盲者眼中的我与你》等,获得欧·亨利奖,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福里奥文学奖。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
精彩书评
一本必读之书,优美、温暖、荡涤心灵,让你大哭一次又一次。
——阿兰·德波顿
埃米·布卢姆是美国的国宝,她写下的词句应该放入句子博物馆。
——迈克尔·坎宁安
布卢姆有一种天赋,能将平凡与深刻、幽默与庄重融为一体。极少有一本关于逝去的回忆录写得如此生意盎然。
——《今日美国》
与大多数书写哀恸的回忆录不同,这本书更具伦理、情感和哲学的深度。
——《爱尔兰时报》
埃米·布卢姆笔下一句话的意涵,比许多作家用整本书所表达的还要丰富。
——《纽约客》
她像契诃夫一样,以冷静之笔书写无法言说的痛苦。她还有一项更为罕见的天赋:她描述幸福的方式,足以让我们沉浸其中。
——厄休拉·勒古恩
不读她,是一种损失。
——《纽约时报》
精彩书摘
终结生命
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对我说:“嗯,为什么要去瑞士?我是说,为什么不去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或者佛蒙特州?那些州有死亡权法律。”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2009年州最高法院裁决通过)、哥伦比亚特区、新泽西州、缅因州、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的死亡权(医生协助死亡)法律要求,你必须是或成为该州的居民(有时简单快捷,但并不总是如此),才能申请医生协助自杀,而且要求你始终神志清醒,经医学评估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并能够向两名当地医生表达自己想死的愿望,通常要表达三次,两次口头,一次书面。
这些法律大同小异,它们故意设定了严苛的门槛。实际上,你必须无比接近鬼门关,才能让医生发誓说你会在六个月内死去。你需要与两名医生面谈,间隔几天,坚决表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自杀倾向或抑郁症,并希望医生同意你的看法。你必须能够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吞下医生开的药物。医生会不会足够体贴地给你开一种药粉,能冲成苦口但容易喝下去的四盎司药水?在某些州,你必须能自己走进药店购买致命的处方药,因为以任何方式向你提供帮助都是非法的。我不确定这一条款的执行力度有多大。
身处绝症晚期,选择死亡并能够独立行动,这是一个刻意设定的狭窄入口。许多人无法满足这一条件。他们无法很好地吞咽。他们的言谈不够清楚。他们不能自行端起玻璃杯或调制饮料。(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帮别人端起玻璃杯是一种犯罪行为。)
那些确实希望结束生命,减轻自己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丧失之感的人——他们在美利坚合众国是不走运的。
突然而缓慢的事
尽管如此,他的失忆还是让人感觉来得很突然:名字消失,不断重复,信息颠倒,约见和用药都很混乱。突然间,似乎所有事情都会让我们争论不休。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因为布赖恩似乎一直在疏远我而哭了很久。那一刻我能看出,他在为我担心,诚心诚意地为他让我难过而感到抱歉,但我也看得出来,他并不真的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哪怕我提醒他想一想我们昨天那场漫长又无意义的争吵,他也还是不知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哭得更厉害了。我们仍然时不时在周日谈一谈,这是一个重要的习惯 :谁伤害了谁的感情,谁欠对方一个道歉,我会更早道歉,他会稍晚一些,但会在晚餐前说出来。布赖恩不是不会用“我没那么说”或者“就算说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类说辞,但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愿意承认错误。一阵怒火之后,乌云会散去,而我的丈夫会更深入一点,通常会给出真诚的道歉(我最喜欢的是 :“对不起,我真是个笨蛋”)。但现在,乌云没有散去 ;道歉很苍白、无力、淡漠。
我感觉他在一块玻璃后面,我拼命敲打着玻璃,对他大喊 :为什么我们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它是从哪里来的?把它拿走!布赖恩关切地看着我,困惑又烦躁,他说的实际上是,什么玻璃?以及,请不要再抱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了。
我打电话给神经科医生,预约了见面时间。等我们去看医生时,紧迫的短期记忆丧失问题已经消退,布赖恩仍然只谈论过去,隔在我们之间的,只剩下玻璃,以及成倍增加的棘手问题。
无法接收的信息
2016年底,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开始看介绍和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网站,还有病人照护者的博客,疯狂关注了一阵子之后,就再也不看了。我停止了阅读,因为我无力承受自己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每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网站的每一页都强调,必须做些什么来应对认知功能的丧失(一开始是约见、手机、驾驶,而后是名字、卫生习惯,个人经历和遥远过去的高光时刻的大块缺失),但其中许多网站关注的是—特别是在早期、诊断后的日子里——虽说丧失了一些功能,这个人依然保留的其他功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切不全都是厄运和黑暗。)一些医学网站还会告诉你,一个人的自我是怎样逐渐消逝的,此时,神经元停止运作,失去与其他神经元的连接,而后死亡。神经元的功能是连接、沟通和修复,而阿尔茨海默病破坏的正是这种内部和外部的连接,首先在内嗅皮层和海马体(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然后扩展到大脑皮质(涉及语言、信息处理和社会行为)。
那些神经元就像大脑的士兵,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年复一年地在大脑中的小路上行军,发起行动,推开一块块巨石。然后,阿尔茨海默病来了,这些士兵的前路被倒下的树木挡住,后路又被悬吊下来的电线拦死。年深日久,这群曾在大脑中上攀下潜、四处征战的精兵强将已然衰退,而外人还远不知这一切。最终(对有些人来说是五年后,有些人是三年后,有些人则是十年后),障碍无法克服。信息无法接收。士兵无法突破新的阵地。唯一的出路就是撤退,只有傻子才会顶着猛烈的炮火继续前行。阿尔茨海默病对我来说如同 1914年,而现在和布赖恩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就像那次著名的圣诞节休战,很短暂,也很美好(德国男孩们爬出战壕,向英国人唱颂歌,喊着“圣诞快乐,英国人”;他们分享香烟,交换纪念品,分享口粮,交换囚犯),而且,不会再有第二次。撤退是明智的。但撤退让我痛不欲生。我想,对布赖恩来说,撤退无关紧要。
那种持续的丧失,持续的瓦解,有时会暂停,但永远不会停止。病人自食其力,或依靠他人的帮助,使用大脑中的替代通路(布赖恩开始称呼每个孙女为“亲爱的”或“小女孩”,而他只会称他的读书俱乐部里的人为“那些家伙”),来尽可能地保持自我的形状完整如昨,直到所有这些都不够用了,直到这个容器,这个由尼罗河黏土和黄麻制成的美丽的埃及罐,开始变软,开始破碎。但破裂不是突然间的事,而是如同麻草被一根一根地抽出来,然后它就不是原来的那个罐子了,它什么都装不下了。你的掌心里只剩一摊黏土和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