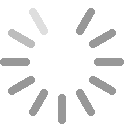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45823912
-
书名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
作者
[美] 韩起澜 著
-
出版社名称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定价
72.00
-
开本
32开
-
译者
卢明华 译
-
出版时间
2024-10-01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知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韩起澜教授的代表作品,探究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上海苏北人群体的全景呈现。韩起澜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历史细节,记录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历经磨难的群体,“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
★“苏北”的范围有多大?究竟是谁界定了“苏北人”?他们为何前往上海,又何以遭受长久的偏见?面对偏见,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学者韩起澜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兼具宏观的族群理论和微观的社会考察,分析苏北人作为族群的历史及其自身的族群认同,解答“苏北人”称谓背后的诸多谜团。
★真实记录苏北人的生活百态。无论是故纸堆里的历史文献,还是生动的口述访谈,如拼图般补全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图景。一本描述扬州风景的书,为何引来扬州人的抗议?家园不保,棚户居民将如何面对?面对“通敌”指控,苏北人会怎样反击?为何一说自己是苏北人,找对象就成了难题?从方言、饮食、穿着、居所,到地方戏、同乡会、职业、婚姻……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历史细节,记录耐人寻味的来沪苏北人往事。
★知名学者李天纲、苏智良,知名文史作家张明扬、资深书评人维舟诚挚推荐!“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苏北人成为上海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努力生存,却备受争议。一个人的原籍为何会引来众多讨论,“苏北人”的称谓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基于丰富的史料,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以上海苏北人为研究对象,从其生活、工作、习惯,以及他者对苏北人的印象与记忆切入,试图揭示其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阐述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反复建构和延续的。苏北既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从原籍的角度寻迹其历史,才能理解族群本身。尽管苏北人所受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在时代浪潮中,但其产生的根源,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
韩起澜,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性别、比较劳工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口述历史。曾获1986—1987年度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奖,代表作有《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等。
精彩书评
大都市内部的族群问题值得关注,只因为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叙述,增进理解,旨在消除偏见,促进融合。我曾参与和见证韩起澜教授的上海苏北人研究,其作品堪称范本!她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构成了海外“上海学”的主力,值得钦佩!
——李天纲(复旦大学教授)
美国学者韩起澜从地理、方言、习俗、文化等角度,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讨论苏北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并就上海人歧视苏北人的原因和程度,提供了精彩的、令人信服的史料和案例,引起我们的兴趣,更促进了我们的深思。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什么是“苏北”,什么又是“江北”?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看完这本书,我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苏北人身份了。
——张明扬(知名文史作家)
看似“天生”的群体身份,实质上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既然苏北人的形成是特殊经历的结果,那也可能逐渐消亡。小群体的成员竭力摆脱原本被污名化的身份标签,通过模仿、隐匿、伪造、通婚等各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融入大群体。可以说,这是一段隐秘的历史。
——维舟(资深书评人)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寻觅苏北
苏北:其地
苏北:其理念
第三章 从移民变为族群
从苏北到江南
上海的客民
棚户区的斗争
争夺的领域:争夺上海文化
第四章 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
上海劳工市场的地区性质
籍贯等级结构的根源
第五章 有争议的族群:苏北人的自我认同
同乡会
自我认同
第六章偏见政治
“江北通敌者”
苏北人的团结
第七章 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后上海的苏北人
当代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不平等的结构
第八章 籍贯的族群含义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棚户区的斗争
19世纪中叶,大批苏北人开始移居上海,许多人在临时的棚户区搭建住所。对一些人来说,搭盖或租赁一间棚屋,是跳出他们过去带到上海的“艉艄船”生活的一步。(在棚户区发展起来以前,纵横交叉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近郊的苏州河和其他河渠挤满了此类船屋。)在许多情况下,移民一直住在船上,直到船体开始崩裂,于是把船体搬到岸上,用以搭盖棚屋。或者,他们仅仅用帆篷搭一个低矮的、隧道状无窗滚地龙以便在夜间睡进去。只有干了几年活以后,大多数人才有能力买些毛竹或麦秆稻草,用这些东西和泥砖搭盖较为耐久的草屋。另一些人盖不起草屋,便以每月0.5—1.5元租一间草棚。
草棚弱不禁风,墙洞权当窗户;一片旧布做门。如能搞到油毡纸,就做屋顶,若没有油毡纸,就用不大能防水的稻草盖屋顶。室内在砖上铺稻草便是床,旧的洋铁罐子作火炉。草屋内常建有阁楼以便容纳别的家庭;大多数草屋里住着至少两家人,有时住四家之多。草屋内用不上自来水。从当地井口里提取的少量井水通常很脏,故许多居民靠从街区消防水龙头取水,工部局每天早晨允许打开水龙头一小时。
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上海到处可见的草屋居民群逐渐演变成街区式的棚户区。查尔斯·尤尔特·达温特在他的《上海:旅游者与居民手册》里描述了这样一个社区:
在苏州河的高河段地区(虹口),从施高特路往北,游客们只要愿意就会看到一个个真正的乞丐村。这些人来自长江以北,江北是个贫困地区。他们的草房是用手脚边能得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盖起来的——泥巴、芦苇、碎砖、旧木板、动物毛皮、麻袋布,还有宣传昂贵肥皂的涂瓷漆铁皮广告牌。那里有的是婴孩、癞皮狗和冬天穿衣、夏天光屁股的顽童。
棚户区是不同时期在上海不同地区出现的。在19世纪晚期,沿黄浦江两岸形成了第一批这样的居民点,大部分是苏北人居住,他们来到上海码头干活。到1900年,浦东潮泥塘、白莲泾、洋泾港、老白渡、烂泥渡都有了棚户区。随着20世纪初在上海东区杨树浦、西区曹家渡和小沙渡(沿苏州河)盖起了工厂,来厂里和沿码头附近干搬运工的苏北移民在上述这些区域建立了棚户区。例如,在工厂建立之前,后来成为棚户区的药水弄原是苏州河沿岸的空地,只有十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到20世纪30年代,药水弄成为一个拥有1000多个草屋居民的居民区。在苏州河北岸,谭子湾成为另一个大居民点。夹在两区之间的苏州河本身就是许多“浮动棚屋”的发源地,这些“浮动棚屋”建在小船上,小船是从苏北到上海跑运输的。与此同时,沿杨树浦路和平凉路一带的杨树浦,居民区一个接一个涌现。
1932年和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导致棚户区扩散,尤其在闸北,那里由于有火车站而遭到重创。闸北新民路、大统路、光复路一带、包括蕃瓜弄的棚户区,全都是这个时期在被炸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最后,到那时为止,新的一波苏北移民在内战期间来到上海,棚户区开始在相对繁华的徐家汇区沿河边出现。例如,肇嘉浜就是在那几年里兴起的。到1949年,将近百万人住在草房里,上海约有322个棚户区,每区至少有200间草房。蕃瓜弄本身约有16000个居民。几乎所有这些棚户区都在大多数中国精英居住的外国租界之外,突出地表明了苏北人在地理上天各一方的处境。棚户区围绕租界形成了几乎完整的一圈。
差不多就是在棚户区出现的同时,工部局官员和房地产投资商就力图把这些刺眼的东西从城市风景线上去除。正如一篇有关试图铲除一个草棚居住区的报道作者简明扼要地说的那样,“租界是一块纯洁干净之地。”临时搭建的草棚被认为“有碍公共卫生和安全”“有碍观瞻”——明显与之格格不入。
自然力量经常促进摧毁草棚的努力。例如,大雨是草棚存在的经久威胁。M.T.邹(音)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了上海工人的住房条件,他描述的情况正是暴雨期间草棚的典型遭遇:
因为该地坑坑洼洼污水满地,居民们最终不得不用泥土填高道路以确保某些通道。但这样一来使四周地势高于室内泥地面。于是,一旦暴雨倾泻,洼地污水泛滥,连泥带水夹杂沼气流进屋内,使之顿成一片汪洋。暴雨过后,笔者目睹男男女女在草棚内行走,污水齐膝深。小孩们被放在用床和桌椅搭成的岛状物上。往往好几天水势不减退。
毫不奇怪,许多草棚殊难幸存。
火是草棚的另一个频发的威胁。火灾经常发生,往往由油灯引起,或者是烧木炭的火炉惹祸。人们在寒冬的几个月里把炭炉拎进屋内烧饭煮菜,并用其余温取暖御寒。在一次典型事故中,一位来自高邮的妇女一手抱着她的婴孩一面在自家的草棚里烧煮,她家住浦东。小宝宝一哭,她就步出户外把宝宝交给她丈夫。这时,靠近炉灶的墙着了火。他们的草棚和许多邻家草棚皆毁于大火,大约500人被火烧伤。类似的大火事件在草棚居住区里司空见惯,有时还毁了整个社区。例如,1949年1月闸北棚户区发生的一场大火烧掉了600间草棚,使2000多人无家可归。从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这一年之内,据日报报道,棚户区至少发生了37次火灾。
火灾的影响也许未必严重,因为当地的救火会对草棚救火往往不那么热忱。例如,1940年一个棚户区发生大火,法租界内离得最近的消防站的救火队员们断定灭火得不到什么好处,因而对呼救电话不作回应。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1月,消防队员对虹口区的火警电话作出了反应。当他们发现火灾发生在棚户区,便无心去救火,声称泥泞小路太窄,救火车进不去。
然而,火灾并不总是无意发生的。放火往往是竭力要铲除草棚的土地所有主的最后手段。例如,1936年闸北裕通路的土地所有者下令草棚居民迁走,那里建有好几百间草棚。居民向租界当局请愿,要求推迟迁出的截止期限。然而问题尚未解决,一场火灾突然发生,在烧了10间草棚以后,租界消防队员才到达。可以肯定,这火是有人纵火。大约400个草棚居民举着旗帜揭露火灾原因,他们游行至巡捕房,要求公布真相。
消灭草棚并不经常借助天灾人祸。相反,从19世纪中期起,租界当局就依靠法律程序来拆除草棚。在1845年土地法规生效时,就已经认定草棚足令外国人厌恶,因而该法规第33条禁止盖草棚——这条法规成为后来公共租界拆毁草棚的依据。从19世纪70年代起,报纸频频报道警方力图拆毁棚户区。例如,1872年的一篇题为《拆毁草棚》的文章描述了这种要消灭公共租界内苏北难民在空地上搭盖的草棚的令人沮丧的做法。巡捕房多次试图驱赶草棚居民,逮捕那些拒毁草棚的人,理由是他们违反租界的法律。该文作者抱怨道:“但这些客民——如果你驱赶他们到东,他们就迁移至西。很难摆脱他们。”20世纪初,草棚仍然令官方心神不宁;继续消灭草棚的图谋被记录在报纸的文章中,文章的标题如《客民占领土地,不欲搬迁》《沿浦江驱散江北客民》。1925年冬天,在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上海工部局用一夜时间拆毁了杨树浦平凉路一个棚户区的1000多间草棚。
正如上述报道所示,草棚居民并未逆来顺受地接受要拆除他们家园的做法。他们抵制这种做法,往往是以高度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抵制,开展斗争,这种斗争以往在有关上海民众抗议的史书中多半被忽视。草棚居民与租界当局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这也许是在1931年苏北洪水泛滥后草棚居民人数大增所致。上海工部局的年度报告如实报告了市政问题,尤其是巡捕房与草棚居民之间的准战斗。例如,1931年的年度报告得意扬扬地宣称大约4590间草棚已被清除。然而,次年报告的作者承认:“大批草棚即通常被称为‘叫化子’棚的存在,乃几年来焦虑不安的缘由。”
1931年决定登记现有草棚,意在逐渐消灭之,因为它们是公共卫生确定无疑的威胁,也构成了严重的火险公害。2041间草棚就这样登记在册。春季难民大涌动,由于紧急状态存在,日常监督放松,大批新的草棚又建起来,乃终于决定通知住户一个月后拆除这些草棚。
这些努力的结果令工部局失望。该年度报告抱怨称,擅自搭盖的草棚“在这一年(1932年)里一如以往添了不少麻烦”。接着报告描述了要拆除草棚的屡屡受挫的尝试:
拆毁未登记的草棚一事先是由公共工程处在10月初开始,后移交给公共卫生处于11月初接办。拆毁这些草棚的工作变成了擅盖草棚者与公共卫生处之间的一场消耗战,因为一间草棚刚被拆毁,马上又盖建起来。草棚居民持之以恒。例如在3月间,一个擅盖草棚的村庄毁于火灾,尽管警方提防,但这个村庄却在两个月内完整地重建起来。
租界当局与草棚居民之间的较量在1936—1937年间达到紧要关头。1935年,上海工部局决定下令租界区东部大约1万名草棚居民拆除他们的草棚。兰路以东的草棚须在1936年7月11日以前拆除;兰路以西的草棚则在8月8日以前拆除。截止期一过,余下的任何草棚将由巡捕房拆毁。同时派巡捕前往棚户区,在每间草棚的门上涂上绿色号码,要求居民向工部局交纳租金(大多数从未做到)。
第一个截止期限到来时,棚户区依旧草棚林立,下午八点钟,工部局派出50名中外巡捕去勒令居民离开。草棚居民表示无意服从;大约2000名居民发动抗议。妇女们拎着便壶作武器,男人手持扫帚,孩子们挥舞着平时用来清刷便壶的刷子,他们指责巡捕房行为“不得人心”。妇女们用便壶围成一垛包围巡捕的墙,巡捕房让了步,同意再宽限五天让居民迁出,否则将加派军队再来。
草棚居民加紧其有组织的努力:来自上海东部棚户区的代表前往上海北部和西部的棚户区,建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各处棚户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代表最终与工部局达成协议,把棚屋拆除推迟到秋天。棚户则答应建立责任制确保不再搭盖新的棚屋。
休战是短命的,9月初的一起表面看来不大的事件引发了新一轮冲突。一个人的棚屋坍塌朽坏,他决定修补他的住房以防漏雨。工部局认为此举违反了不得建新棚屋的暂时禁令,乃派巡捕拆毁了他的棚屋。邻居聚众抗议;巡捕用棍棒把众人打了回去,打伤了一些人。这就促使棚户的那些所谓的娘子军动员起来,她们用马桶刷子打巡捕,将马桶内的污物扔向巡捕。《申报》记者说:“臭气不堪!”许多妇女被捕,被押往杨树浦捕房,罪名是“妨害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其整修翻新而引发事件的那间棚屋在随后的骚乱过程中毁于一旦。
经此事件,棚户与工部局之间的冲突减少了,这多半是因为工部局明显地舒缓了它要消灭棚屋的决心。但是,在工部局于1937年春宣布拆毁棚屋的新的截止限期后不久,棚户居民再一次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住所。棚户居民在每条街道上集会,集会之后大约上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吁请保留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请求于4月遭到拒绝后,他们发动了示威。为同4000名示威者较劲,工部局不仅派出警力而且派了一个排的上海义勇队俄国团士兵,他们配有机关枪。示威者于是撤退,派代表团会晤工部局助理秘书长T.K.何(音)。双方达成妥协,据此,代表们同意负责拆毁476间棚屋并清除残存的废稻草和竹棍。反过来,工部局提供被左倾的《中国周报》编辑们称之为“怜悯金”的费用,每个棚户14元(折合4.05美元)。只有在全部476间棚屋悉数拆除后才发钱。
这项计划的结果不得而知,也许落了空,因为计划执行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不管怎样,被拆毁的少量棚屋,同战时难民新盖的大量棚屋比起来,肯定相形见绌。战争结束时棚户数目如此之大以致消灭棚屋成为国民党领导的市政府的重大项目之一。1945年底,市府颁布法律禁止搭盖新棚屋。政府官员解释说:“为确保大多数市民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牺牲少数集团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夏季卫生问题和冬季火险问题,这些棚屋的确是全市市民的一个危险。……棚屋必须清除!”该法律没有发生效力,仅仅过了一年又通过了一项内容几乎相同的法律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次规定专门由警察巡逻负责执法。奉命巡逻的警察向棚户居民发表一项声明,称他们不会亲自动手,只是执行政府命令。这些法律——即使加上警察巡逻——似乎很少对棚屋问题产生影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时期棚户数目有所减少;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倒是由于来自苏北的难民使棚户队伍膨胀起来。1949年中国共产党最终接管上海时,面广量大的棚户成为它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尽管它并未彻底清除棚屋,但由于建造了棚户居民租用得起的公共住房,同时禁止农村地区人移居上海,因而大大减少了棚户数目。
1949年以前的历届政府清除棚屋的尝试,不管多么持之以恒和坚决,都不曾取得哪怕是少许的成功。只要农村移民继续流入上海,棚户区的扩散就不可避免,就像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经历一样。从政府角度看,清除棚屋之战吃了败仗。然而此战仍然意味深长,因为即使它没有明目张胆地针对苏北人,但实际上是针对苏北人在上海的城市风景线上所占据的一席安身立命之地。这种企图是要把这同苏北人相联系的贫困清除出去,或者至少是迁往该市的边缘地区。
然而,不能把拆除棚屋的企图理解为江南精英与苏北移民之间的直接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受外国支配的上海工部局在袭击棚户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间接地说明了外国在上海的存在促进了苏北人这个类别的建构。在外国人看来,至关紧要的事实是棚户区的扩散,给现代城市的形象抹了黑。至于究竟谁住在这些棚屋里则多半无关紧要的。
但是,对于观察和参与这场斗争的中国精英集团来说,出身原籍至关重要。一篇杂志文章写道:“南市、闸北、浦东、徐家汇和土山湾的贫民窟居住着江北穷人。”一家报纸的一篇有关闸北棚户区的报道称“江北穷人正在盖草棚”;另一篇报道提到“江北客人住进贫民窟”。把棚户区归结为苏北人并冠以江北棚户区的称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同如此冒犯外国精英的一种中国现象分离开来。于是,棚户区就成为苏北人这个类别被建构并充实以象征性含义的中心舞台。
在棚户区问题上的斗争,对于苏北人建构他们在上海的身份,具有不同的但很重要的含义。苏北人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住所时,他们是作为棚户居民而为之,不是作为苏北人这么做的。然而这些斗争极有可能在棚户区居民中输入一种在上海的新的群体意识。即使这些斗争并未导致苏北人身份的明确表述,但很可能锻造了苏北人之间的联盟,这些苏北人以前经历过并坚持更多以地方为基础的团结。
前言/序言
前 言
本书论述上海的族群,撰写本书起意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城。1977年,我初次来到埃尔帕索,同两位朋友一道,从事对卷入1972—1974年法拉制造公司罢工的奇卡纳女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奇卡纳女工在罢工期间形成的联合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听说这次罢工也被描绘成奇卡纳和墨西哥的女工之间的分裂和对抗,这让我们最初感到困惑。我们在1978年和1979年回头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这些分裂派系夹杂着像埃尔帕索那样的边城所具有的族群含义。
1979年我来到上海,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棉纺厂女工史。在那时,我总是能想起在埃尔帕索采访过和结交过的妇女们,我们曾试图解开关于她们团结和摩擦的谜团。也许是无意识地,在埃尔帕索令我全神贯注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研究,因为不无巧合的是,上海女工内部(特别是在来自江苏省北部和南部的女工之间)的分隔,成为本研究的主导旋律。长江对江苏的分割,令人回想起(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格兰德河所代表的分隔,该河把埃尔帕索同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分隔开来。根据上海以原籍为基础分隔的最初提示,我加紧采访和阅读文件资料以探索这种分隔对女工生活的含义和对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
然而,在有关女工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中,有一个基本问题依然无法回答,这关乎来自江苏南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分隔的根源,尤其是江苏北部土生土长的人即苏北人地位低下的根源。有两点认识使我有兴趣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第一,分隔并不限于棉纺厂,而是事实上
在上海形成了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第二,这种分隔及对苏北人的偏见在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于是,本书在刚开始时的部分,试图分析在上海出现这种偏见的根源。起初我设想的是写一部关于上海苏北人的历史。
由于有关苏北人资料的极度匮乏,好几次我差点放弃这个项目。但最迫使我想放弃的是一个惊人的认识,我在已经工作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我一直以为,包括我的大多数知情人也都以为,谁是苏北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个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部的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它可以按地理、语言或经济状况来界定,但是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我的课题和我的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在我眼前仿佛都消失了。
我没有中止我的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反而最终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殚精竭虑去拼凑上海苏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被建构的过程及其发挥的功能。在我开始把籍贯(比如苏北人的籍贯)看作社会建构的类别时,也开始考量籍贯表现族群含义的方式。我越来越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族群关系,这种分析以前从未应用于中国,也许是因为压倒多数的人口都是汉族身份吧。于是,本研究最终没有成为关于上海底层社会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关于创立中国族群学的研究。
本书并不僭称是上海苏北人的完整历史,也不按编年次序编排。相反,每一章都探讨苏北族群被建构和受到争议的历史场合。导论之后的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团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第二章探索同苏北有关的种种含义,分析其作为社会类别的产生以回应苏北移民来到江南和上海的现象。上海的苏北移民群体的形成和上海当局把这个群体边缘化的企图是第三章的主题。第四章聚焦于苏北人在上海的从业经历,分析劳工市场是如何产生族群,又是如何受族群影响的。第五章将我们的视角转向苏北人本身,探索他们如何建构他们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如何对精英集团炮制的苏北身份进行抗争和抵制。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出现了,在那时,苏北人的地位成为公众辩论的主题,这个社会类别史无前例地遭到冷遇和受到挑战,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尽管头几章全都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第七章则论述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苏北族群的存续和对之进行的商讨,第八章也是本书最后一章,是对籍贯的族群含义方面的反思。
社会类别的含义以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我质疑社会类别的目的产生了一个术语学问题:如何指涉我所要描述其历史的那个人群。我在本书从头到尾使用苏北这一术语来指涉江苏北部,即从长江至淮河古道之间的核心地区,苏北人则指该地区的居民。当我使用苏北这个措辞时,系指那些当初在上海被称为“苏北佬”的人,而不论其确切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如此用词是希望苏北一词被理解为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在上海,最通常用来指涉江苏北部的是江北而不是苏北。事实上,许多上海人一听说我在研究苏北人就好奇地看着我,当他们一听到江北这个术语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很清楚了。我使用苏北这个术语是因为江北这个术语在上海已成为贬义词,即使在以前也许并非如此。
我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本项目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特别感谢罗丽莎,在我十分确信我的课题已经告吹时,她帮助我理清了各种可能的思路,令人振奋。黛安娜·怀利花费很多精力在纽黑文听取了我关于籍贯族群的最初步的想法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在我动手写书时,柯临清、韩倞、贺萧、玛丽莲·杨以及罗丽莎投身到我们在周六开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其中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讨论我的作品。他们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评点数易其稿的本书各章,易稿次数之多可能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位留心记忆所不及的。
另有许多人也对本项目作出了贡献。裴宜理和曼素恩不仅极其慷慨地让我分享了她们拥有的有关上海工人的资料,而且还对整部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点。我也感谢戴慧思、史景迁和白凯阅读和评论了本书最后一稿。戴维·蒙哥马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例证。多年来,许多同事拨冗莅临饭局和会议,讨论有关苏北人的理念和提供知情人线索,他们是:安敏成、白彬菊、周锡瑞、康无为、李中清、托马斯·罗斯基、萧凤霞、王绍光、范力沛、魏斐德、华志坚、魏爱莲、蔡九迪。韩森贡献了她研究宋代的经验,她帮助我正确地分析有关资料方面的问题。米凯拉·迪莱昂纳多慷慨地贡献了她在有关族群的人类学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长。
然而,倘若不是上海众多人士慷慨襄助,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份书稿,要不是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批评指正,恐怕连主意也不会有。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同意我采访的在上海的苏北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了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其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赵念国,常常竭尽全力安排访谈。我感谢筱文艳、马秀英和上海淮剧团的成员帮助安排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苏北之行。我在上海期间,邓裕志、徐新吾、薛素珍、陈曾年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
好几项学术基金使我从事这项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学术基金来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王氏中国问题研究所、耶鲁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格里斯沃尔德基金会。这些资助使我得以借重赵小建、申晓红、梁侃的非常宝贵的研究襄助。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查尔斯·格伦奇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有时还会悄悄提醒,这正符合我对编辑的预期。劳伦斯·肯尼对手稿做了仔细的校订。邓尔麟代表出版社对手稿所作的评论充满真知灼见,促使我对自己的分析精益求精。
有几位人士对本项目作出了不那么直接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我感谢莉莎·菲奥尔—马塔和路易丝·默里提供了纽约西村的一套公寓,使我能花一周时间对本书的尾章进行反复思考;伊迪丝·赫德提供了一所可以眺望旧金山的房子,使我在那里修改定稿;也要谢谢罗莎和马娅自己玩耍、讲故事;莉西娅·菲奥尔—马塔拓展了我在思想上和地理上的想象力。 最后,从我俩1977年前往埃尔帕索起,历经无数次去中国的研究之旅,贺萧始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严峻的批评者,也是一位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