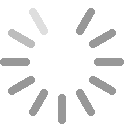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59678744
-
书名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作者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
出版社名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定价
59.80
-
开本
32开
-
译者
章艳 译
-
出版时间
2024-10-01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社科读者、教育行业从业者、教育社会学研究者
1、本书作者尼尔·波兹曼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与传播理论学者,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者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精神领袖,地位仅次于麦克卢汉。其代表作“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对于技术崇拜、机器意识形态、浅薄娱乐文化的批判,不仅在传播学界,而且在广大普通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本书是波兹曼透彻反思教育问题的代表作。波兹曼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的本质与方法,以及童年与学习的意义有着深刻的思考。本书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总结,延续了他在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中提出的媒介技术批评思想,对于现代教育系统的问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批判。
3、追逐功利、沉迷消费、文化对立……比起审视文化与教育的现状、思考教育的真正目的与意义,当代教育工作者更加关心电脑、网络这些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而这种“技术崇拜”恰恰让整个教育系统深陷危机。波兹曼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全面揭示了当代教育的问题根源,在技术时代坚决捍卫人文主义价值,为迷失方向的教育指出正确的道路。对于当今的教育者与学习者,以及所有关切文化现状的人来说,波兹曼清晰严谨的讨论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一生关注教育问题。从最初在小学执教,到在纽约大学设立媒介环境学专业,培养出一批著名的传播学者,作为教育家的波兹曼不断思考着教育的本质与方法,在其媒介-技术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致力于培养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教育理论。这些思考的结晶就是《教育何用》。
在本书中,波兹曼针对美国教育系统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讨,指出美国教育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教育工作者沉迷于教育的技术方法,却忽视了教育的根本意义与目的。作者批判了几种流行的叙事,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分离主义;同时揭示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塑造学生对民主、团结、多样性、批判性等人文主义价值的认同。
作者简介
作者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教育家,媒介环境学的开创者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精神领袖,长期任教于纽约大学,担任文化与传播学系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教育学、文化与技术批评。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代表作有“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以及《教育何用》等。
译者 章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理论研究方向为文化翻译和翻译美学。译有《娱乐至死》《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应得的权利》《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重访美丽新世界》等作品。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神灵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章 那些失败的神灵
第三章 那些失败的新神灵
第四章 可能奏效的诸神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球飞船
第六章 堕落天使
第七章 美国实验
第八章 多样性法则
第九章 文字编织者/世界创造者
尾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在思考如何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学校教育时,成年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工程问题;另一个是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个工程问题和所有这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个技术问题。这是关于手段的问题,通过这个手段年轻人将获得学问。它设法解决的是何时何地学习的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学习应该如何进行。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任何自认为有价值的有关学校教育的书籍都必须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学习工程性的一面往往被夸大了,被赋予了名不副实的重要性。老话说得好,一样东西百样做,而这一百样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学习也是如此。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是认识事物、感受事物、观察事物、记忆事物、运用事物、联系事物的最佳方法,而其他方法都不及它。事实上,这么说是低估了学习,让它沦为机械化的技能。
当然,有许多学习过程确实只是机械化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存在某种最佳方法。但是,如果你要通过自己学到的东西使自身脱胎换骨—获得顿悟,改变观念,拓展视野,从而改变你的世界—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
我在这里用的词是“理由”,这和“动机”不同。在学校教育的语境下,动机指的是一种暂时的心理事件,一旦有了动机,人就会产生好奇心并且能够集中注意力。我无意贬低动机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把它与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动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做某些事情—例如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的话、参加考试、做家庭作业、忍受学校里不喜欢的东西—的理由混为一谈。
这种理由有点抽象,并不是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很难描述。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理由,学校教育就无法发挥作用。为了使学校有意义,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必须有一个可以侍奉的神灵,或者,最好有几个可以侍奉的神灵。如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神灵,学校就毫无意义。尼采有句著名的箴言正好可以用在这里:“一个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忍受任何生活境遇。”这句话适用于生活,也同样适用于学习。
简而言之,若想让学校教育终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失去目的。
所谓要侍奉的神灵,我指的不一定是上帝。人们认为是他创造了世界,而他在圣典中提出的道德禁令赋予了无数人生活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学习的理由。在西方世界,从13世纪开始,在其后的五百年里,上帝足以成为建立学习机构的理由,其中有教导儿童学习阅读《圣经》的文法学校、有培养牧师的重要高等学府。即使在今天,对西方的一些学校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学校来说,它们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侍奉上帝或真主,赞美他的荣光。但凡是这种情况,学校不会出现棘手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危机。也许人们会争论哪些科目能最有效地促进虔诚、服从和信仰,也许会有学生对教义心存疑虑,甚至会有老师压根儿不信教。但对这类学校来说,最关键的是它们有一种超验的精神理念,赋予学习以明确的目的。即使是怀疑论者和不信教的人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应该学习什么,又为什么会抗拒学习。有些人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应该离开。
几年前,我与伊利诺伊州埃尔萨的普林西皮亚学院(Principia College)一位很受欢迎的杰出哲学教授进行过一次令人感到难过的谈话。普林西皮亚学院曾经是,而且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是基督教科学派教会唯一的一所高等院校。他告诉我,在普林西皮亚学院的那几年是他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他现在选择了一所非宗教大学工作,因为他不再相信基督教科学派的信条。其实他在那里上课的内容并不包括对那些信条的讨论,更没有专门讲授它们。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不满。但他不再相信那个机构的宗旨,每一门课程,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充斥着某种他无法接受的叙事的精神,所以他选择了离开。我一直希望这位失意的教授最终能找到另一个可以侍奉的神灵,另一种可以赋予他的教学以意义的叙事。
带着几分疑惑,但更多的是抱着信念,我把“叙事”这个词用作“神灵”的同义词,不过这个神灵(god)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God)。我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不仅是因为“神灵”这个词有神圣的光环,不能随便用,而且还因为它让人想到一个固定的人物或形象。但是,这类人物或形象的宗旨应该是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一个观念,并且在我看来更应该是引向一个故事—这可不是随便什么故事,而是一个讲述起源、展望未来的故事,一个构建理想、确立行为准则、提供权威来源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要给人以延续性和目的感。我使用的“神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伟大的叙事。这个叙事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复杂性和象征力量,使人能够围绕它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使用的这个词类似于阿瑟·库斯勒在《失败的神灵》中所表达的意义。他的意图是想表明,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验,更不是一种经济理论,而是一个全面的叙事,讲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还希望表明,尽管共产主义蔑视传统宗教的“非理性”叙事,但它自己也依赖于信仰和教条。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诸神一定会失败——远非如此,尽管确实有很多神灵会失败。我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出现过几个灾难性的叙事,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几个神灵都承诺会有天堂,最终却只通向地狱。如果你继续阅读后面的章节就会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灵,它们俘获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但我相信,这还不足以为人们的生活或学习提供深刻的理由。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就会发现,我相信,有一些叙事可以促进生活和学习,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给予它们足够的关注。这些是为我们服务的神灵,也是我们要侍奉的神灵。
尽管如此,我在这里的意图既不是要埋葬哪个神灵,也不是要赞美哪个神灵,而是要说,我们不能没有它们,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是神灵创造出来的作品。我们的才华在于我们有能力通过创造叙事来创造意义,这些叙事让我们的劳动获得了意义,歌颂我们的历史,阐释当下,并为我们的未来指明方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这些叙事不一定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在许多不朽的叙事中,有些细节与可观察到的事实并不相符。叙事的目的是赋予世界意义,而不是科学地描述它。衡量一个叙事真伪的标准在于其产生的后果: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归属感?是否能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依据,对不可知的事物进行解释?
你会认识到,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约瑟夫·坎贝尔和罗洛·梅将其称为“神话”。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故事的创造性来源和心理需求,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它们称为“幻象”(illusions)。人们也许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时,也有和弗洛伊德相同的想法,这么说不算牵强。但是,我并不是要从学术角度来区分这些术语的微妙差别。关键是,无论怎么称呼它们,我们都在通过叙事的方式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历史和未来。没有叙事,生活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学习就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学校就是关押人的地方,而不是关注人的地方。我的这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