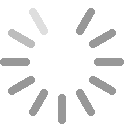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45220117
-
书名
本雅明书信集
-
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
出版社名称
光启书局
-
定价
198.00
-
开本
32开
-
编者
[德] 特奥多·W. 阿多诺,[以] 格肖姆·肖勒姆 编
-
译者
金晓宇 译
-
出版时间
2024-08-01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目前最全面的本雅明书信集,以一手材料揭示其思想演变,20世纪重要思想家悉数登场
◆300余封珍贵信件,跨度30年,见证一代天才在流亡岁月里的友谊、孤独与纯粹意志
◆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门槛上的永恒旅行者、德国文学唯一真正的批评家的心灵之旅
◆德国著名哲学家特奥多·W. 阿多诺、20世纪德裔重要思想家格肖姆·肖勒姆联袂编注的经典版本,金晓宇倾情献译,力图还原本雅明非凡的写信风格
内容简介
书信集收录德国思想家本雅明信件300多封,由肖勒姆、阿多诺合力编辑,编年编定,加以注释。展现了本雅明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文笔,揭示了思想轨迹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家及各类人物的关系,对于理解20世纪前半期欧洲文化和思想人物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在这本书信集中,本雅明谈到了文学、思潮、创作、社交、旅行、工作和生活,对卡夫卡的反思贯穿了这本书;20世纪最重要的一批思想家如汉娜·阿伦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雷纳·玛丽亚·里尔克、恩斯特·布洛赫、卡尔·克劳斯、马丁·布伯等人悉数登场。新一代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那一代欧洲知识分子澎湃的思想脉动。
作者简介
作者 |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文学家、思想家,因其博学和敏锐而享誉世界,被视为20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他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独到,著作宏富,著有《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评歌德的<亲和力>》《摄影小史》《柏林童年》《德意志人》等名著,尚留下六册书信集。作为众所周知的思想家,其论著丰富的解释力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俨然成为重审现代性与欧洲文化史的关键节点。
编者 | 格肖姆·肖勒姆(1897一1982),以色列思想家,年轻时因研习灵知主义同本雅明相识,并成为至交。
特奥多·W. 阿多诺(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流亡期间,他和本雅明在巴黎和圣雷莫共度了很多时光。
译者 | 金晓宇,1972年生于天津,自由译者,所译语种以英语、日语、德语为主,所译图书涉及文学、艺术、音乐、电影、思想学术等类。现居杭州。
精彩书评
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写信人,显然,他写信时充满了激情。尽管经历了两次战争、希特勒帝国和流亡,他的很多信件依然被保存了下来……书信成了他的一种文学形式。
写信在僵硬的文字媒介中模拟出一种生气。在信中,一个人可以否认孤立,但仍然保持疏离、孤独。
——特奥多·W. 阿多诺
这些信件带我们穿越本雅明完全退隐,甚至可以说隐匿的岁月,直至他作为作家和记者活跃的时代。
——格肖姆·肖勒姆
即使是这些信中较为随意和一时乐观的内容,也笼罩着巨大的悲伤。它们是在欧洲陷入噩梦时寄出的......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本令人欢欣鼓舞的书。它颂扬了智力激情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思想和神经系统即使在或特别是在面对个人的逆境和悲伤时,也有能力投身于抽象的投机兴趣之中。
——乔治·斯坦纳《纽约客》
瓦尔特·本雅明和格肖姆·肖勒姆之间的关系无疑是20世纪非同寻常的友谊之一。本雅明是评论家,而肖勒姆是历史学家,他们不仅都是首屈一指的创新思想家,改变了各自领域的知识视野,而且他们还就至今仍显得紧迫的知识和精神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斗争。还有一点是,尽管他们的人生道路大相径庭,尽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最考验人的灵魂,但在人性层面上,他们友谊的道德纤维被证明是如此坚韧和顽强。本雅明和肖勒姆的书信是出于一种坚忍不拔的孤独感而写成的——不是完全的孤立,而是天才的孤独感,他们逆时代潮流而行,提出了政治现实无法满足的“激进要求”。
——罗伯特·阿尔特《新共和》
目录
导言 I ………………………………………………1
导言 II ………………………………………………5
1910—1928 年间书信 ………………………………15
1929—1940 年间书信…………………………………484
附录 ……………………………………………………847
精彩书摘
我主要在与一本书扭打,它是一个魔鬼,一部典范(一本书中的一段,霍拉旭–施莱格尔会说),我与这条恶龙格斗了十分钟,就像往昔圣乔治所做的那样。我把它读完了!我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四百九十九页。阅读这本书时,我体验到了对这个蓝色的、大腹便便的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版式怪兽的真正愤怒,我每天带它去草地或进入树林,然而它回到畜舍(也就是我的背心口袋)时,看起来更胖,而不是更瘦了。
——《6 致赫伯特·贝尔莫尔》
亲爱的赫伯特:
科学是一头母牛
它哞哞叫
我坐在阶梯教室里倾听!
(事实上,在这里,我能够独立思考学术问题的频繁程度大约只有在柏林的十分之一。)
现在请原谅这封疯狂的信。如果你想了解实际情况,让我的父母给你看我的一封二十页长的信。你不能要求我重复实际的描述。你也会知道,在各个方面,第一个学期都是一个开始和混沌的时期 (要打折扣的……有一些阳光)——并且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什么比写理性的信更难的了。
另一方面,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一定很容易。
——《7 致赫伯特·贝尔莫尔》
我的岳父母是我们的仅剩的经济依靠,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依靠不是很牢固,他们愿意作出最极端的牺牲;他们坚持让我成为一名书商或出版商。现在,我父亲甚至拒绝给我资金来做这件事。但是,看样子,我不能再表现得像是我还在追求以前的目标,还不考虑成为一名大学讲师。而且无论如何,暂时我将不得不一边从事一些小市民的工作,一边在夜间秘密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会是一份什么工作。(这个月我做了三次笔迹分析,因此赚了 110 马克。)
——《90 致格哈德·肖勒姆》
你应该听到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字。我最近决定翻译他漫长的小说系列《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主要小说。我将翻译三卷本的作品,《所多玛和蛾摩拉》。报酬并不是很好,但可以忍受,以至于我认为有必要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此外,如果翻译成功的话,我可以指望作为译者被永久地认可,例如像斯蒂芬·茨威格那样。也许我们曾经偶尔谈到普鲁斯特,而我曾经断言他的哲学观点与我的有多接近。每当我读到他写的任何东西时,我都会觉得我们是志趣相投的人。
——《145 致格哈德·肖勒姆》
当我感觉最糟糕的时候,我把所有与普鲁斯特有关的事情都推到一边,完全只为我自己工作,并写了一些我非常喜欢的笔记:首先是一篇关于水手的极美的笔记(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一篇关于广告,其他的是关于女报贩、死刑、年市、射击馆、卡尔·克劳斯——全是苦涩的,苦涩的药草,我现在在菜园里热情地培植它们。
——《155 致朱拉·拉特》
在《堂吉诃德》中,读者的笑声挽救了资产阶级世界的荣誉,与之相比,骑士的世界显得统一而简单。相反,杜米埃的笑声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他看透了它所标榜的平等:也就是说,作为不可靠的平等,正如它在路易–菲利普的绰号中所夸耀的那样。在笑声中,塞万提斯和杜米埃清除了他们认为是历史假象的平等。平等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形象,更不用说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了。在《人群中的人》中,可能仍然闪烁着通过喜剧成分来驱魔的可能性。在波德莱尔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倒不如说,他人为地加深了平等的历史幻觉,这种幻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根深蒂固。
——《310 致特奥多·W. 阿多诺》
我已建议汉娜·阿伦特把她那本关于拉赫尔·瓦尔哈根的书的手稿提供给你。应该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寄给你。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大力划水,逆着使人虔诚和愧悔的犹太研究的潮流而上。你最清楚地知道,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读到的关于“德国文学中的犹太人”的一切,都是让自己顺着这股潮流而下的。
——《309 致格哈德·肖勒姆》
像往常一样,当一个项目变得非常紧迫时,我就会承担一些琐碎的任务。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剪辑作品,就像我的书信选一样,目的是展示法国大革命对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甚至对后来的一代,直到 1830 年的影响。在撰写时,我再次遇到了一些被德国文学史故意掩盖了一百年的事实。想象一下,当我仔细阅读了克洛卜施托克的两卷颂歌后发现,其中包含更晚的颂歌的第二卷的所有作品中,有五分之一是关于法国
大革命的,我感到的惊讶。
——《316 致玛格丽特·斯特芬》
前言/序言
(特奥多·W. 阿多诺)
有一件轶事与通信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本雅明作为写信人的独特之处。有一段谈话谈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区别;例如,在现场交谈中,出于人性化,人们说话不那么正式,会使用更随便的现在完成时,而非语法上要求的过去时。本雅明对语言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但他不接受这个观点,并强烈地提出了质疑,仿佛被触及了痛处。他的信件是说话声音的形象,通过讲话来书写。
然而,这些信件的克制却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而这证明使广泛的读者群能够接触到它们是正确的。真正以五彩缤纷的反光体验当下生活的人被赋予了过去的力量。书信形式是过时的,在本雅明在世时已经开始变得过时了;但他自己的书信不会因此而受到指责。本雅明有一个特点,只要有可能,他就用手写信,尽管打字机早已盛行;书写的身体行为给他乐趣——他喜欢制作摘录和誊清稿——就像他不喜欢机械辅助工具一样:在这方面,《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论文,就像他的思想史的许多其他阶段一样,是对进攻者的一种认同。写信提出了个体的一种要求,但如今在推进这一要求方面却无能为力,正如世界不再尊重这一要求一样。当本雅明说不再可能讽刺任何人时,他接近了这一事实;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也是如此。在把每个人都降格为一种功能的整体社会结构中,不再有人有资格在信中描述他自己,就好像他仍然是一个未被理解的个体,正如信中所说:信中的自我已经有一些表面的东西。
然而,从主观上讲,在这个经验解体的时代,人们不再愿意写信了。在此期间,技术似乎正在剥夺信件的先决条件。鉴于更快捷的通讯手段和时空距离的缩短,信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信件的实质本身也正在消失。本雅明给它们带来了一种古旧和奔放的天赋;他庆祝了一个正在消逝的机构与其乌托邦式的恢复的婚礼。诱使他写信的原因可能还与他的经验方式有关,因为他把历史的形式——信件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看作需要破译的自然,发出了具有约束力的命令。他作为写信人的态度接近于寓言作家的态度:书信对本雅明来说是自然历史的插图,说明在时间的毁灭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他自己的书信,由于一点也不像活人转瞬即逝的表达,因而获得了它们的客观力量:那是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塑造和区分的力量。眼睛为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损失而悲伤,仍然如此耐心而紧张地停留在事物上,而这种耐心和紧张必须再次成为可能。本雅明的私下声明引出了他的信件的秘密:我对人不感兴趣,我只对事物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