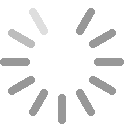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101165838
-
书名
甲申前夜·大晦
-
作者
刘鹤 著
-
出版社名称
中华书局
-
定价
78.00
-
开本
16开
-
出版时间
2024-04-01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1.刘鹤2024年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全面展示明末社会图景与市民百态。
2.悬念丛生、情节跌宕,一柄“妖刀”剖开王朝腐朽肌理。
3.大明、朝鲜、日本,三国往事共同演绎一段东亚的历史悲歌。
内容简介
《甲申前夜·大晦》以明末为历史背景,以松锦战役中浮海逃回的辽东明军下级军官刘破虏在崇祯十六年冬天的一系列诡异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光里,官员、军人、百姓在大灾、大疫、大战中的人生百态和命运沉浮。
作者简介
刘鹤,高校教师,作家,编剧,《澎湃新闻》《南方周末》专栏作者,新浪微博“2020、2021、2022年十大最具影响力历史大V”,全甲格斗运动员。代表作《天亡之秋》《兵者不祥》《扪虱卧谈录》等。
精彩书评
刘鹤懂史,懂武,懂战争。他爱刀剑,爱技击,并非寻常的纸上谈兵。每次和他聊天南地北,总能感受到当今社会中少见的侠气。如今他这个现代剑客写历史与侠义,实在太令人期待了。读书要读内行的。——陈嘉上导演
目录
北直隶·真定府·野狗 _1
北直隶·真定府·失鹿 _13
崇祯十五年·杏山·赵子龙 _29
北直隶·真定府·瘟神 _41
京师·宣武门外·服妖 _61
京师·德胜门·箭上有神 _73
京师·德胜门·依柳将军 _89
万历十七年·辽东·萨尔浒 _99
京师·德胜门外·吞羯 _121
京师·南城兵马司·避疫 _143
京师·果子巷·南下 _157
京师·南城兵马司·喇唬 _171
京师·大时雍坊·避瘟楼 _195
大时雍坊·陈宅·捉鬼 _221
宣武门外·天主堂·炮神 _247
宣武门外·大时雍坊·倭城 _259
大时雍坊·故衣胡同·射狐 _275
大时雍坊·避瘟楼·破贼 _305
宣武门外·南城兵马司·剑鬼 _331
萨尔浒·界藩山·波平 _355
澄清坊·骆家大宅·陀螺精 _381
崇文门内·勾栏胡同·孙六 _407
九州·岩屋城·生试、死试、荒试 _431
正阳门下·味羽斋·大银国 _459
正南坊·南城兵马司·相剑 _481
东江米巷·会同南馆·大晦日 _505
尾声 _525
后记 _529
精彩书摘
骆养性继续追问:
“戚、李治军有何异?为何李不如戚?”
刘破虏答:“李成梁以心治军,戚继光以法治军。以心治军,则必有人衰心死之时,强兵亦不复存;以法治军,则人死而法不灭,军法代代相传,则强兵生生不息。”
骆养性更加专注,忙说:“细说来听!”
刘破虏谈论兵法也意兴正酣,不再避讳,直率地答道:“成梁、如松父子,以子侄兄弟之心厚待士卒,其麾下作战日久者遂纳为家丁,俱改姓李,吃穿住用,不啻五品之官,故如松云其麾下殁于碧蹄馆之兵非兵也,皆手足兄弟也,古人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焉能不强?然成梁、如松既殁,恩养之心不再,手足之情不存,骄兵悍将垂垂老矣,止留跋扈之气,萨尔浒闻贼一声号响,未见贼而自相践踏而死者千人。
“戚继光以法治兵,军法森严,赏罚分明,令行而禁止,浙兵皆选垄亩之间忠厚农民,既无骄矜之气,又无剽掠之习,若论骑射武艺,恐去北兵甚远,然其进则齐头,退则并足,若得命令,则刀山火海一往无前,枪矛如林不敢缓步,未得命令,纵满地金银亦不敢取一分,全军覆没而不敢退一步,故其不在兵强,亦不在将强,而在法强。故戚驾鹤之后,其麾下将领如吴惟忠等,仍能得其法而练强兵,遂有朝鲜之捷。”
骆养性怔怔地看着刘破虏,突然站起来径直向他走来,刘破虏连忙作起揖来,骆养性忙扶住他,拍着他的背说:“只知辽兵中猛将如云,不知辽兵中还有如此智将,今日真大开眼界,受教了。只怨与刘大人结识太晚,不能早些向朝廷举荐英才。”
刘破虏有些不知所措,嘴上客套了几句,赶紧把包袱拿了出来,说:“大人恩德,下官无以为报,惟有精甲一领,献给大人。”
骆养性饶有兴趣地接过那沉甸甸的包袱,刘破虏头上泛起一层细细的汗珠,包袱里正是那夜不收身上的锁子甲,用猪鬃细细刷去了血迹。刘破虏已经领教了骆养性的城府,把这死人身上扒来的东西献给骆养性让他有些惶恐和忐忑,但他确实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让骆养性多看哪怕一眼的物件了。
骆养性打开了包袱,用手从冰凉的锁甲表面滑过,说:“唔?像是瓦剌人的锁子。”
破虏忙说:“此乃撒马尔罕回回所造锁甲,不同寻常恶铁,乃用精钢丝作环,环口锤扁钻孔砸铆,坚牢非常,下官曾以弓射之而不入,箭镞两刃铁皆反卷,实精甲也。”一边指出锁甲背部把肚射击造成的刮痕给骆养性看。
骆养性显得很高兴,这反而加深了刘破虏的不安,担心他看出了端倪。骆养性把甲展开看了看,又用手反复摸了摸被箭射过的位置,啧啧称奇,叫人将甲收到库里去,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心满意足地啜一口茶,意犹未尽地说:“方才说到戚李治军之高下,刘大人所见实在洞彻,然刘大人只说了治军之道,却未说为官之道。”
刘破虏忙说:“请大人指点。”
骆养性悠悠地说:“正如刘大人所说,李成梁以心治军,以情驭兵,故李家之军如参天大树笼罩辽东,兵兵将将盘根错节势不可分,故成梁位极人臣,本朝开国以来所罕有,其诸子一封再封,备极恩荫,纵参告成梁之使自辽东至京师不绝于道,而成梁不损一毫,何也?成梁下狱,辽东翻天。
“戚南塘以法治军,故人去而法留,法留则军留,故虽有戚家军之名,实大明之兵也,成梁之兵虽无李家军之名,实李家之兵也,故成梁屡有大过而位极人臣,寿终正寝,南塘偶有小嫌而一贬再贬,困厄而死。”
刘破虏头上又开始冒汗,骆养性见了,又哈哈两声,安抚他说:“我虽是武官,却不甚精通军务,刘大人身经百战,却不谙为官之道,逢此乱世危难之时,幸得结识,今后当以兄弟相称,共谋报国之举。”
刘破虏不胜惶恐,起身一边作揖一边应承,同时留意着窗外的天光,希望能在午时之前赶回衙门。
骆养性却一点没有让他回去的意思,反而把话题引向深入,说:“你我既以兄弟相称,则百无禁忌,军务辽事,刘兄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刘破虏唯唯诺诺地说:“一定,一定。”心里却想起晚年凄惨穷困潦倒而死的戚继光,和把肚说的那番话:“你这朝廷,文的不拿武的作人看,读书的不拿当兵的作人看,关内人不拿边疆人作人看,南人不拿北人作人看,做官的不拿老百姓作人看,人看人作牛马、鸡犬!上下里外,都是诓、骗,事事俱坏极了!这样的朝廷,你纵死在此处也是枉死!”
骆养性没有理会刘破虏的若有所思,啜一口茶,态度突然严肃了些,问道:“我闻辽事败坏以来,奴贼日益势大,现麾下各色汉军,已有十万之众,刘兄征战辽东多年,想必见过,言官指从贼者皆辽民辽兵,前朝熊廷弼亦有辽人从贼之说,当真?”
刘破虏心头一紧,脸上一热,答:“确是实情,附贼之汉军多系大明军民陷于贼者,亦有奸佞投献,受封伪官、伪将。贼境约有辽民三四十万户,生丁一百余万口,汉军约七八万,约有红衣炮六七十位。”
骆养性微微一笑,似乎对刘破虏的坦诚很满意,继续问:“奴贼狞狠,百倍于虏,历次入关荼毒直隶、山东,每破一城必屠尽军民,老幼不留,济南、临清之惨,塘报字字滴血,不难推揣辽东情形,袁崇焕亦报自天启朝以来,辽民为奴贼所屠者不下百万,其中岂无从贼者之父母兄弟?何故辽民投贼如蚁附,甘为仇寇之奴,而不愿为大明之民?”
刘破虏脸上阴云密布,思索良久,咬咬牙答道:“奴贼法度,强者生,弱者死,视人如牛马猪狗。无用者如老弱病残,悉杀之,妇幼收为奴婢,青壮者若孔武有力,则以其武力强弱依等纳之:降兵、降将有能骑善射或能领兵治军者,往往善待,授予官职,使其仍领旧部,发给金银、牛马、女子、奴仆;有能操炮者,或携炮投献者,尤其厚遇,使其自成一军,号乌真超哈,重兵之意也。故虽奴贼屡屠辽民,而投贼者络绎不绝,盖乱世之秋,青壮不顾老弱,男丁不顾妇孺也。”
刘破虏这一番话避重就轻,并没有说出辽民辽兵在大明苛政恶吏下民不聊生的惨状,他知道,京城里最开明睿智的大人们,也只承认大明朝败在器具、败在战技战法,甚至愿意承认败在军事制度,而绝不愿承认大明朝败在人心,在他们看来,辽人投贼是因为和胡人混居日久,沾染胡俗,气类相习,是天生的奸民,如果不是朝廷从关内调去的军队都不堪一击,不得不仰仗他们守住山海关,早就该将这些不服管教的奸民严惩不贷。刘破虏从关外逃回京师两年,早已对此心知肚明。
骆养性点点头表示认同,说:“我闻奴自夸云杀我山东兵如刈筑,当真如此,或奴作大言?”
刘破虏答:“大抵不差。奴数次入关,对我关内之兵强弱了如指掌,颇轻关内之兵,且奸细甚多,我山海关内外各兵虚实,尽为其所知。奴军中早年谚云:‘辽人好浪战,浙兵善鸟铳,川兵习枪棒,湖兵只管走,此皆不足畏,只怕大炮筒。’今奴大炮齐备,益轻我兵。下官去年随周延儒出城御敌,亲见奴在我京畿重地大军之侧解鞍饮马,卸甲嬉戏,视我军为无物。且如今我朝文武大小官员,多是花钱买的,文官不知军事,武官弓马不熟,故关内之兵,虽十倍于奴,仍难抵御。”
骆养性再次点点头,沉思片刻,忽然笑了笑说:“卖官鬻爵,实在官场痼疾,大小废材如附骨之疽,百无一用。唯一好处,赖以得见刘兄耳。”
刘破虏心头一紧,复又脸上一红。紧的不是骆养性对自己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这一点他早就已经领教过了,他心头紧的是骆养性掌握了如此多关于他的信息,显然非常看重他,然而骆养性真正的目的,至今尚未显露半分。他脸红的是他虽然极度排斥和抵触买官卖官,然而他自己这官却也是六百两银子买来的。
刘破虏担心谈话继续深入下去,这一紧一红的情形会越来越多,况且天色不早,他不知道那一百个烧饼能稳住这帮叫花子一样的残兵多久,他已经在飞速盘算退去的借口。
骆养性还在笑,似乎已经洞悉了刘破虏的内心,他开口说:“天色不早,刘兄还有军务在身,我也不便强留,改日待刘兄安顿好衙门,定要把酒畅谈。刘兄家中熟知奴情之山后军士,也一并邀约,必兴尽而归!”
刘破虏凭空得了这台阶,忙不迭客套几句就要退下,骆养性又笑眯眯地调侃了一句:“那就祝刘兄旗开得胜,剿尽喇唬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刘破虏几次三番领教骆养性的本事,已经不再对此吃惊了,他一改拘谨的态度,反而附和着哈哈了几声,行了礼转身昂首走了。
骆养性一手握着绦带,拇指摩挲着绦带上冰凉的青玉带,脸上带着骄矜自满的表情看着刘破虏的背影,仿佛将军在看自己新置办的一口宝刀。
忍耐了许久的骆祚久一脸不满的从后堂走了出来,骆养性头也不回,仍看着刘破虏离去的方向,慢悠悠地说:“听过了?”
骆祚久行过了礼,有些急切地说:“京城大族,半数已作南迁准备,满朝文武,多只留一人在京,妻小俱送南京安顿,南下车马络绎不绝,人人想的都是南方的事,父亲何必与一达子整日商谈关外那些不着边际之事!”
骆祚久失了态,骆养性却也不恼,淡淡地说:“并非达子,不过辽军一老兵官。”
骆祚久忿忿地说:“父亲难道不闻‘辽人半贼也’?初一领饷,十五投贼,为贼骗开城郭,从贼架炮攻城,父亲派去山海关的锦衣卫,至今可有一人回事?此等关外兵痞,粗莽武夫,笼络何益?!”
骆养性并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他:“太平年岁,京城里一把倭刀售价几何?”
骆祚久被问住了,他胡乱答道:“许是十几两吧。”
骆养性摇摇头:“太平年岁,寻常倭刀一柄不过二两,倭样腰刀不过一两,粗者贱至几百钱,倭扇一柄二十两。如今倭样刀一柄直价五两不止,有铭之倭刀几十上百两求而不得,却不见肯以刀易扇的蠢人,何也?思自保耳。人亦如刀扇,太平年月,文人贵,武人贱,乱世危局,文人贱,武人贵!
“你不见那白广恩,不过是一草寇,无非能杀赢几阵,如今不但沐猴而冠,称得一声将军,皇帝召他来见,他顿兵不来,不但不降罪,皇帝还要拿两万两银子安抚他哩。”
骆祚久好像懂了一点儿,又好像没懂,问:“父亲是想让这辽军护送我等南下?为何又不见父亲吩咐家里准备车马?父亲不怕这辽军是清国细作?”
骆养性似乎对儿子的悟性有些不满,他转过身来,盯着骆祚久的眼睛说:“南下?我大明朝虽有两京之制,然而南京朝堂,岂有善人待你鸠占鹊巢?北官南渡,龃龉必多,党争之祸,近在眼前!江南膏腴之地,豪商巨贾、官宦世家如过江之鲫,况南人善科举,在北京为官之南人一旦南渡归巢,其根基岂是寻常北官可比?我骆家在京城虽属大户,但若南渡,田、地、宅既带不走,又无处可卖,隆冬跋涉,路途叵测,家产必损失过半。生逢乱世,一则真刀真枪,二则真金白银,到时为父空有太子太傅左都督的一品衔,也未必保得住这一家老小富贵。”
骆祚久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眼界和心思都太浅,所以只能领悟一半,他明白了为什么骆养性执意不打算南渡,却不明白骆养性到底要留在北京做什么。
骆养性对儿子的驽钝并不意外,也不指望他明白,直截了当地说:“为今之计,止有与虎谋皮。流贼虽势大,却是乌合之众,各股皆有头目,一时听闯贼号令,却并非部曲,那闯贼虽有大志,不过流贼中一霸主,终非皇帝之命。奴贼虽远在关外,种种制度悉从中原,耕战皆有其法,数次入关,数万大军进退有度,纵横千里,不输中原名将。今有辽兵数万从之,又得红衣大炮,则关内坚城,旦夕可下。
奴酋黄台吉(皇太极)已自称天子,其志已不在关外,而在天下矣!三桂亦辽人,岂不知贼意?无非据关守望,待价而沽也,故今虽乱在关内,大定之事,却在山海之外。”
骆养性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骆祚久:“派去山海关的人,可有消息?”
骆祚久答:“前后三拨人马入关,均被吴三桂留下,日给吃喝用度,但不许见他,父亲手书已请人转递,亦无复信。我人进出均有兵丁监视,如同软禁,只留一人回事,言总兵留锦衣卫军官关上小住几日,讨教军事,不日即送回。”
骆养性沉思片刻,摇摇头说:“前有袁崇焕事,吴三桂已成惊弓之鸟,终不信我,惧我差人诱他回京治罪,又不愿开罪于我,故扣留差官不遣。”
骆养性又沉思片刻,缓缓地说:“三桂必降清……”
骆祚久猛地想起刘破虏刚才说的话:“奴贼法度,强者生,弱者死,视人如牛马猪狗。……降兵、降将有能骑善射或能领兵治军者,往往善待,授予官职,使其仍领旧部,发给金银、牛马、女子、奴仆。有能操炮者,或携炮投献者,尤其厚遇,使其自成一军,号乌真超哈,重兵之意也。故虽奴贼屡屠辽民,而投贼者络绎不绝,盖乱世之秋,青壮不顾老弱,男丁不顾妇孺也。”
不禁被骆养性的心思惊出了一身冷汗,骆养性的大胆和悖逆让他畏惧,骆养性的缜密和远谋又让他折服,他羞愧于自己没有这种胆量和韬略,不配做眼前这个人的儿子。
骆养性没理他,自顾自地说下去:“自古得北方者南征易,得南方者北伐难,奴贼志在天下,一道长江岂能拦得住?南渡不过妇人之见,南渡南渡,愈渡愈南,渡去崖山吗?刘破虏随祖家诸将在关外征战多年,大凌河降人之中,岂无其故旧?三桂系大寿外甥,山海关之辽兵中,岂无其亲朋?他手下那通晓奴语的达子,更有妙用。
“方才你也听见,奴贼法度,强者生,弱者死,我今一苦于手中无精兵强将可倚,二苦于无路与奴通款,三桂之路既绝,则我必有他路。刘破虏若不是清国细作,便是我的刀,他若真是清国细作,便是我的桥。”
骆养性说的直白露骨,吓得骆祚久大气也不敢出,汗水顺着后脑流过颈子已是冰凉,又顺着脊骨淌下来,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骆养性的算计早已超出了他的见识和理解,他思索了半天,问出了一个很蠢的问题:“依父亲之见,刘破虏是不是清国奸细?”
骆养性笑了,摆摆手说:“我倒愿他是清国奸细,可惜不是。不过是穷困潦倒一老军官而已,有些城府。”
骆祚久说:“父亲三番五次给他银子,原是此意,父亲又如何知道他是真穷,不是装穷?”
骆养性说:“若是装穷,怎么会冒着犯讳的险,献一领死人身上剥来的甲给我?”
骆祚久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骆养性,似乎不明白他是如何看出甲是从死人身上剥来的。
骆养性命人将那甲从库中取出,让骆祚久去看。骆祚久细细查看,并未在甲上找到一丝血迹,又用鼻子嗅嗅,只闻到防锈的猪油味里,混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白酒味。骆祚久复用手摸了摸锁甲的后背位置被箭射过的痕迹,疑惑地摇摇头,表示仍然看不出玄机。
骆养性斜他一眼,幽幽地揶揄道:“倘你试射坚甲,第一箭会从甲背面射吗?”
骆祚久呆立在当场,手里的锁甲如水银泻地,哗啦一声摊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