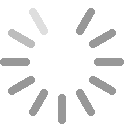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旧风旧雨》由著名小说家丁天、著名作家孙小宁及董宁文作序,全书以”人“为中心,共收入作者靳飞历年来所写的怀念文章、人物小传等共39篇。在这些文章所涉及的人物中,既有严文井、季羡林、启功、许觉民、张中行、胡洁青、周汝昌、舒芜、绿原等文化学术界耆老,也有叶盛长、梅葆玖、新凤霞、梅葆玥、林连昆、牛星丽、金雅琴、韩善续等戏剧界著名人士。书中还有数篇关于梅兰芳、张二奎、刘赶三、孙菊仙等的研究随笔。本书还收录了作者所写的关于金凤、丁荫楠、冯远征、坂东玉三郎等中日各界杰出人士的文章。这些人物,作者多是与之交往或研究多年,对其有着深入了解,谈来自有独特深刻处。
内容推荐
《旧风旧雨》是作者靳飞所写京城文化名流的交往实录,文笔谨严,见解独到,文中所叙多为作者亲历亲闻,史料性、趣味性、文学性融为一体,是一本不多见的写人的随笔集。本书为随笔集,开卷随笔文丛之一,融史料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目录
达夫文痕人迹
寂寞书斋笔底波澜——贺张中行翁回想录完成
代张中行翁赋得黄英
怀念绍棠
又一种美丽的逝去——哭新凤霞阿姨
送别萧乾先生
遥祭梅葆玥
松柏常青——纪念胡絮青老人
谁爱京剧,我就爱谁——哭叶盛长先生
雅的律尺——闻启功先生归道山有作
一个人的烦恼与一个不烦恼的灵魂——东京旅中悼严
文井先生
悼梅先生绍武
别许觉民先生
怀念蓝天柱同志
悼季羡林先生
跳出舒芜的概念认识舒芜——怀念舒芜先生
关于苦难与幸福——送别绿原
林连昆逝世感言
清明怀牛星丽
悲悼能乐师关根祥人先生
谁人有此闲性情——怀念周汝昌先生
梨园旧艺妙通神——怀念刘曾复先生
你们属于我的城市
民国史躲不开梅兰芳
《贵妃醉酒>:一出旧戏的变革历程
梅葆玖先生的最后一程
让我们重新回到信仰与热爱
梅氏的新京剧与新文化
终生为记者豪放犹少年——记金凤
丁荫楠之史记式电影
谈坂东玉三郎
坂东玉三郎略记
张国荣与坂东玉三郎的最后一面
想起十几年前的冯远征
年少争传张二奎——张二奎纪
优孟衣冠伴老驴——刘赶三传
宏廓大嗓令人豪——孙菊仙纪
每一件事都是复杂的——也说沈从文与范曾
编后记 王亮鹏
试读章节
达夫文痕人迹
仅是通过作品去认识作家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文如其人的话不可全信。说远的,李太白,名句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这大抵是醉后胡吣,没有酒力作怪的时候,只恨天子不来呼,一旦听到风声,立刻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了,李白其人究竟如其哪句文呢?再说近的,由轻而重,轻的,读罢《老舍文集》十六卷,仍是不能想到老舍是清晨要坐在马桶上喝一杯咖啡而不是豆汁儿;重的,周作人笔下何等清淡且是腴润,我永爱他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然而,在他身后二十余年公开的他早期与友人通信,津津乐道人是人非,如:”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无此意而凤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凤举自己尚未有印绶,惟其必有一颗印可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既酸又羡。由周文推想其附逆总觉不可思议,由他对布衣的不甘想其袍笏登场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所谓出仕,不是顺理成章吗?
文,有时是人的障眼法;人,有时也做文的包装盒。人原是复杂,作家又是复杂的人。固然,我们也可以只理会作品而不问作家其人,譬如小孩子把”朝辞白帝彩云间“念得琅琅,却未必记住谪仙人的大名。但是,假若对文学作品不止于读,要进一步求解,求会心,想躲开作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便有了一簿自古至今无论如何都清理不完的,作家与作品的乱麻账。
我现在所要说的是:郁达夫在现代作家中迥异的风格,他尽其最大限度地在作品中公开着自己,无论美的丑的,生活的精神的,他因而也就活在他的作品的世界。他的作品流传至今,他的人也依旧是鲜活的。
我们很难断定文如其人与文非其人孰高孰低。况且文学本就未必要求真实。可是,人生于世,我们所惯见的,是人人将其心灵努力封锁,仿佛胸腔内装的是铁皮匣子,我们便不能不觉郁达夫的可贵与亲近。他的好处不仅仅是便宜研究家,读他的作品,直如我们又多了一位赤诚的朋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那么,就来谈谈我们的这位朋友,虽然我的所知是十分肤浅。
达夫平生有两种重要的苦闷吧,一种是新与旧的迷茫,一是才与俗的不融。这两种苦闷的焦点是他的三次婚姻悲剧。
他在热烈地追求后来与他共同生活十三年的夫人王映霞时写的情书,解释他的第一次婚姻:”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做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地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地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和我生活,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地漂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
郁的这番解释,实在只是套用的那时反对包办婚姻的公式化说法,与其具体情况多有出入。被郁称作”我的女人“的孙荃,和郁同为浙江富阳人,两人是”三岁的时候定下的“,我在旅中无从可考,但在他一九一三年东渡扶桑时,临行前一日还约会了已具有其未婚妻身份的孙荃。这次约会亦是初会,郁的印象是,”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彼时孙家欲促完婚,达夫以即将赴日,”母老矣“,不能为之养妻子为由婉拒。可他在见过孙荃的次日,寄诗给孙荃,口气则俨然以未婚夫自居,而且定下五年之期,”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又:”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更有《为某改字日兰坡名日荃》一首:
题君封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距”赠名“二日,达夫又赠孙荃诗云,”相思倘化夫妻石,妆在江南我玉关“。P1-4
序言
天地原是好家乡
董宁文
我与靳飞兄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初的一天上午,那天我如约前往他指定的湖广会馆,初次见面即很投机,你一言,我一语,当然基本都是听他说话,其时靳飞兄大约也才三十出头吧,但所谈及的人和事大多都是京城文化界的老先生,我对其中的不少老先生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次的见面,起因是张中行先生的指引。记得是与靳飞兄见面的前几日,我去拜访行公,聆教之后,行公说,你以后如果想要找我,或者想要知道一些我的近况,可找靳飞和庞旸两位即可。并在一张小纸片儿上写下了两位的名字,并告诉了二位的电话给我。记得那天应我之情,行公在我所带的一本小册页上写下了一页手迹以为纪念: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戊寅六月张中行
从此以后,我与靳飞兄始终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联系,因为他一直比较忙碌,但是我们对彼此的近况也都是比较关注的。
回过头来再说下那天见面的情况,虽然至今已有十八年的时间,但是所谈及的一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书中提及的由靳飞兄在湖广会馆为季羡林先生米寿所策划的那场堂会所描述的场景令人心驰神往,那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活动,只是最终没有达到预期而令人更增添了遐想的空间。那次堂会,我的老朋友范笑我因公务去京,正巧赶上,也值得一记。
那天我们还商量好一同去医院看望萧乾先生,所有的细节都已谈妥,只是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早上,靳飞兄突然来电话,说是文洁若先生表示暂时不宜去而未成行,也因此错过了与萧乾先生晤面的机缘。后来,我与文洁若先生交往颇多,在萧乾先生去世后也曾去过他们家几次,但也只能看到原封未动的萧乾先生书房的模样,看到墙上很多大大小小萧乾先生的彩色照片。有一次,文洁若先生还告诉我萧乾先生的骨灰也存放在家里。
虽然无缘见到萧乾先生,但是我还是因文洁若先生的热心帮助而藏有他们夫妇二人的一十本签名本,萧乾先生的签名本是他生前所签,细心的文洁若先生还在每本书上钤上了二位的印章,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书缘吧。
现在手头正看着靳飞兄给我写的一张镶着金边的日本镜片,上面写了两句话:平生若无功名累,天地原是好家乡。这张镜片写好,他手边没有带印章来,只好压上了一方”北京湖广会馆“的方形印章。记得靳飞兄当时说,这样也不错,正好记下我们在湖广会馆的见面。
几年后,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再次见面,再后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南京来一两次,我们在凤凰台饭店的开有益斋以及他来南京必住的古南都饭店多次见面闲聊,我还介绍了南京的几位书友与他见面闲聊。最近四五年,靳飞兄似乎更加忙碌了,好在去年我们因他研究梅兰芳《贵妃醉酒》的专著《梅氏醉酒宝笈》一书的出版事宜再次联系上,后因故未在我手里出成,而由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后来,靳飞兄觉得过意不去,说他手里还有一本《旧风旧雨》似乎更适合我们”开卷“系列,也就因此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书中三四十篇文章都不太长,但涉及的文坛、学界以及戏剧影视界的人却不少,一一读来,似又听到靳飞兄的娓娓道来,深感亲切。这其中的妙处自不待言,还是请读者诸君细细品味吧。
书中新加的几篇有关梅葆玖先生的文章记录了靳飞兄与玖爷多年来的交往以及深情。记得四月初的一天晚上,靳飞兄从北京打来一个长长的电话,我们彼此畅聊了一番,其中谈及玖爷的病情不容乐观,大家心情都很沉郁,二十多天后,梅葆玖先生即仙逝。
一个月前,靳飞兄命我在书前也写一篇序,我本想此书已有两篇妙序,如果我再写一篇一定会有累赘之憾,但转念一想,写一点我与靳飞兄过往的实录,或许也不无不可,故此写下以上的一些闲话,以记录一二我与靳飞兄的书缘往事吧。
丙申五月初四于金陵开卷楼南窗
后记
靳飞先生在《谁爱京剧,我就爱谁——哭叶盛长先生》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近年我作过不少悼亡的文字,有出版社和我商量编作一集,这却是我无论如何都不忍心做的,因为我自己就无法面对这样一本书。我那还算年轻的生命,有一半以上的部分是和我所怀缅的逝者一起度过的。“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不忍心做的“事由我替他做了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本《旧风旧雨》。
我们常用”旧雨新知“来比拟自己的朋友之多、交游之广,这是惯见的词汇。而用”旧风旧雨“作书名,却是靳飞先生的发明。书中有关金凤、丁荫楠、冯远征、坂东玉三郎的文章,本就是关于”旧雨“的友情记述,且不必细说。而那些纪念文章涉及人物,先生与他们的交往都在廿年以上,作这些文字的时候,忍看朋辈成新鬼,心际必定风雨如晦,期间所蕴含的沉痛容易想见。
书中还收了京剧大师张二奎、孙菊仙、刘赶三、梅兰芳,现代文学作家郁达夫等的研究文章,先生于这些前人,不但是隔代知音,亦肯作”解味人“,探幽寻赜,替他们述说浮生烟云,不致使之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其实这类文字,还有很多,皆是不可多得的妙文,读来如饮甘饴,令人难忘。限于篇幅,只好割舍掉了。
我读集内文字,最为感动的还是那些悼亡之作。同寻常的纪念文章不同,在先生笔下,一个个风采各异的文化老人,立体般地出现我的面前,引发了我对那些已逝文化老人的无限遐想,不与其时的遗憾也就常常萦绕心头,只得叹息余生也晚。
在这部分怀人文字中,除个别的几篇,先生着力于考察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文化贡献,而把个人的情感、对往事的回忆,以寥寥数笔化入其间。这样的写作,无疑使老先生们的文化功绩汇人中华文化的主脉之中,使之形象更为饱满,既有史家识断,又不乏人间温情。
不唯在纪念文章中,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明确意识更贯穿书中其他的文字里。我读先生的文章,常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个中缘由,想来就在于先生是自觉地以史家意识在写作。先生又是极讲究笔墨的,因此,这种明确的史学意识便融化在先生那犹如涓涓流水的文字当中。草蛇灰线,不易寻见罢了。
先生深知历史考察与当时真实之间的隔膜与距离,因此他又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复杂的。这种基于人性复杂难料的同情之了解,或可作为评判人物时的一种必要考量。
张伯驹先生曾讲过自己倾尽全力收藏文物的原因,是希望那些文物可以”世传有序“。而当年那些文化老人不遗余力地扶助如先生这般的年轻人时,分明为着两个字:传灯。文明的赓续,大概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而现在,先生的这本《旧风旧雨》,又举着文明的灯火,照亮着后来的行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