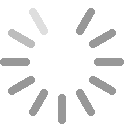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04368201
-
书名
纷纷扰扰男女情
-
出版社名称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定价
29.80
-
开本
16开
-
出版时间
2013-02-01
-
编者
梁刚建 编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
- 查看全部

内容简介
《纷纷扰扰男女情》中选收的回忆文章,都是名家们饱含感情写师友的精心之作,脍炙人口,可谓篇篇珠玑,编选者李群、李聪、曹誉峰、黄善灵的工作只是用“男女情”这条线把它们串在了一起而已。
《纷纷扰扰男女情》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录
导言
第一篇 张爱玲与胡兰成——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二篇 钱钟书与杨绛——最平凡的相濡以沫
第三篇 沈从文与张兆与——穷书生的爱情故事
第四篇 石评梅与高君宇——陶然亭的合葬碑
第五篇 丁玲与胡也频——漂泊的爱情
第六篇 丁玲与瞿秋白——是媒人还是恋人
第七篇 丁玲与冯雪峰——半生情缘
第八篇 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共艰危
第九篇 鲁迅与萧红——良师益友
第十篇 鲁迅与许羡苏——亦真亦幻师生情
第十一篇 徐志摩与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精彩书摘
一见倾情一世孽缘
1944年初春某天,胡兰成在南京一座庭院的草坪上,翻看着《天地》第11期。他被一篇题为《封锁》的小说深深吸引,被作者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
几天后回到上海,胡兰成立即去拜访其文作者张爱玲。首次登门他却碰了壁,只得从门缝中塞进了一张纸条,写下自己的电话,悻悻而归。第二天,张爱玲给胡兰成打电话,告诉他要上门拜访。就这样,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与一个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
不久后,因为身处异地,更因为胡兰成的滥爱,二人分道扬镳。正是这短短的一段爱情生活,给张爱玲以后的人生染上了灰暗的色彩。
《张爱玲记(节选)》文/胡兰成……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值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级。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她的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连不以为她是美的,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何如何,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甚么叫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
我竟是要和爱玲斗,向她批评今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还讲我在南京的事情,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我而且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听她很老实的回答。初次见面,人家又是小姐,问到这些是失礼的,但是对着好人,珍惜之意亦只能是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
张爱玲亦会孜孜的只管听我说,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她也一般的糊涂可笑。我的惊艳是还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她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后来我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回家我写了第一封信给张爱玲,竟写成了像五四时代的新诗,一般幼稚可笑,张爱玲也诧异,我还自己以为好。都是张爱玲之故,使我后来想起就要觉得难为情。但我信里说她谦逊,却道着了她,她回信说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甚么事冲犯,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后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
因为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相,翌日她便取出给我,背后还写有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这送相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把相片给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没有神魂颠倒。
各种感情与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先,但有意义。而不是甚么的意义,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
……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只是说话说不完。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甚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但爱玲喜欢这种刺激,像听山西梆子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而且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甚么,爱玲亦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我的囿于定型的东西,张爱玲给我的新鲜惊喜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旧小说里常有人到了仙境,所见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爱玲的说话行事与我如冰炭,每每当下我不以为然,连她给我看她的绘画,亦与我所预期的完全不对。
但是不必等到后来识得了才欢喜佩服,便是起初不识,连欢喜佩服亦尚未形成,心里倒是带有多少叛逆的那种诧异,亦就非常好,而我就只凭这样辛辣而又糊涂的好感觉,对于不识的东西亦一概承认,她问我喜欢她的绘画么,只得答说是的,爱玲听了很高兴,还告诉她的姑姑。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牵牛织女鹊桥相会,喁喁私语尚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
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如此只顾男欢女爱,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随又我去南京,让她亦有工夫好写文章。而每次小别,亦并无离愁,倒像是过了灯节,对平常日子转觉另有一种新意。只说银河是泪水,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
……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日: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抚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晴。”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叫我“兰成”,我当时竟不知道如何答应。我总不当面叫她名字,与人是说张爱玲,她今要我叫来听听,我十分无奈,只叫得一声“爱玲”,登时很狼狈,她也听了诧异,道:“啊?”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荷花娇欲语,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房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但是我们又很俗气。
……选自《今生今世》P4-7
前言/序言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文/曹鹏本丛书中选收的回忆文章,都是名家们饱含感情写师友的精心之作,脍炙人口,可谓篇篇珠玑,编选者的工作只是用一条线把它们串在了一起而已。
这条线,除个别例外,有点像修辞里的顶针格,名家忆名家,后一个名家写前一个名家,更后的名家又写后一个名家。这种情景,可以借用卞之琳的名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来描绘。
一回顾历史,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乃至40年代,中国的文坛繁荣兴盛,名家名作硕果累累。民国的文人活得意气风发,虽然有战争,有动荡,有迫害,有贫穷,但在精神上是自由而健康的。这种文化上的生机勃勃在本书所收文章里反映得很清楚。
才学是文人彼此成为朋友的基础,这也就是所谓的共同语言,但与此同时,文人都有个性,甚至是极张扬或咄咄逼人的个性,这又是很多文人结怨成为对头的原因。
以鲁迅与郁达夫为例,他们的性格与为人处世的作风皆有天壤之别,可是两人交情甚好,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写悼念文章也直言不讳两人性格的反差,鲁迅在世时也曾公开讲到这点。鲁迅在文章里写道:“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日: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日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鲁迅《伪自由书前记》)用现在的眼光看,民国文坛的斗争激烈,鲁迅更是以战士的姿态,攻击过一大批论敌,可是,当时光的尘埃落定之后,后人看得越来越清楚,即使是鲁迅骂得最不堪的章士钊、梁实秋、陈西滢、顾颉刚,也都是青史留名的杰出学者,学术成就与贡献有的甚至不在鲁迅之下,这倒有些像武侠评书里英雄所标榜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不学无术的草包与混混,在民国文坛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不光没机会成为鲁迅这样的人物的朋友或学生,甚至没机会成为敌人或对手。
曹丕有句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同是文人,相轻虽不可取,但也还可以理解;可怕的是那些自己并非文人的对文人“轻”起来,也就是武大郎开店“狗眼看人低”高人莫来的嫉贤妒能,才是妨害文化学术的邪恶力量。不幸的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二鲁迅对青年的感情,如同萧红用女性特有的直觉指出的,是一种“母性”,也就是发自内心的爱护与关心,在力所能及时给予机会与帮助,从精神到物质,自发的不求回报的付出。这也是多子女家庭里长子的角色所决定的性格特点。虽然鲁迅经常委婉地抱怨有青年学生不仅不感恩报恩,甚至会反目成仇或算计师长,如高长虹、李小峰,但是他对待青年还是一片热心。
鲁迅在民国文坛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旗手,他在身后更享有极高的地位,甚至被神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青年中的声望与人气。1936年10月19日他逝世后,《大公报》发表一篇相对客观的小评论,言语中对鲁迅的成就有所褒贬,编辑萧乾为此不惜与大公报负责人撕破脸抗争,由此可见鲁迅的形象何等神圣不容侵犯。
鲁迅的葬礼之隆重,在民国文坛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在当时重丧的社会背景下,葬礼大都要靠家庭张罗,大操大办往往要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如“旧王孙”溥儒葬母那样,而鲁迅遗属孤儿寡妇根本没有经济上与精力上的条件大办丧事,事实上,鲁迅能备享哀荣,除了他的朋友们出面,更多的靠的就是学生一辈的青年。
鲁迅对文学工作者的影响是至深至大的,孙犁就是一个例子,他对鲁迅心悦诚服,几乎亦步亦趋,他在成名后甚至按鲁迅日记所附购书账,逐一照单全收地订购图书。孙犁学习鲁迅的作风,培植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
孙犁提携过的文学青年,最著名的要数莫言了。在莫言还在当兵刚尝试业余创作时的1984年4月,孙犁为《天津日报》写了一篇《读小说札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当年孙犁在中国文坛有一言兴邦的影响,所以,莫言自己说:“几个月后,我拿着孙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2012年10月,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姑且不论此奖的价值与份量如何,作为中国大陆作家第一个得奖者,莫言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这在1984年孙犁写那篇文章时,肯定是没预料到的,他的一句话,成就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评不评发表在地级市文学刊物上的一个青年作者的作品,在孙犁是可有可无之事,可以说,孙犁评莫言,只是兴之所致的偶然,不过,偶然多了,就有必然,所以,对于青年与学生,能多给一些提携与帮助,在长者、尊者、为人师者,是责任与义务,广种薄收,甚至广种未收,也比不种要好得多。
成功者耕耘也许不需要回报,但是收获时人们会更尊敬播种者。
三同是帮助晚辈后生,效果都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或“鲤鱼跃龙门”的大恩,帮助者的态度不同,对被帮助者来说感情也就不同。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有句意味深长的话:“慷慨大度与抠门小气一样令人不好受,感激涕零和忘恩负义一样令人憎恶。”写尽了师生或朋友或亲戚之间,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微妙复杂关系。这也许可以解释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
郁达夫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不久,他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沈从文因此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提携。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与其说是对文学新人沈从文的肯定与鼓励支持,不如说是浇冷水,文章显露的是郁达夫特有的不加掩饰的优越感与悲天悯人情怀,在这里沈从文只不过是一个大文豪借以发愤世嫉俗的议论的可怜道具。对于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有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也许正是最蔑视自己的人,这样的关系真是无可奈何。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时,沈从文在代序里写下了一段文字:“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这种表述方法耐人寻味。现今社会,人名排列成为一门学问,特别是在报纸与广播电视新闻上,顺序谁先谁后,讲究大得很,别武断地把这贬斥为形式主义官本位作风,要知道,中国的国情确实有通过先后顺序字里行间皮里阳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写文人时,字句的掂量推敲会格外用心。
沈从文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的小说与散文发表数量巨大,可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他没有留下关于郁达夫的回忆或纪念、追悼文章。相比之下,他写过悼念徐志摩的文章。沈从文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把郁达夫与张资平合论——沈从文是精研《史记》的,对太史公的笔法颇多体悟,这篇虽非老子与韩非合传体例,但鉴于当时张资平在文坛的口碑以及后来的形象,把郁达夫与张资平并列论述,已经是春秋笔法,明显不全是敬意。
沈从文对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谈起郁达夫,因为是对恩人的晚辈,言辞中肯定会表达知遇感恩之情,这也是一个有教养的长者应有的礼数。也许我是强作解人,我认为,对于作家与学者,还是文章与著作中的评价更能表明真实感情与态度。在书面上不置一辞,或写一篇可以作字里行间解读的文章,同样是一种评价。
四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他们都既是文学报刊编辑又是小说散文作家,可谓志同道合。因此,巴金笔下的沈从文,就与郁达夫笔下的鲁迅异曲同工。
在交情友谊之外,巴金对沈从文的推崇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也对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被边缘化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予以声援。
从五十年代开始,文人学者在各种运动中受打击迫害,成为司空见惯寻常事,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很少有谁敢于仗义直言。巴金晚年致力于反思自己与“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性影响,因此,他悼念沈从文的文章,表达的不仅是个人感情,还有着左拉“我控诉”的义愤。他对沈从文逝世后国内报道既晚又简短表示谴责,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真不是有什么指示或精神在发挥作用,而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演艺明星与富豪老板才是热点,新闻业实际上已经失去对文化学术人物的关注兴趣。这也算是“文革”后遗症吧。
五在作者与回忆文章的主人公是朋友或夫妻时,视角不会是仰视,而是平视——反而更接近真实面貌。同样回忆鲁迅,萧红是高山仰止体,虽然很生动、亲切,但更多程度上可能是年轻女作家带着有色眼镜满怀敬慕的感情看到的鲁迅,不由自主的美化了。而郁达夫笔下的鲁迅,更可信,也更平凡与生活化。郁达夫当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不在鲁迅之下,所以,在沉痛悼念时,也只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描写,事实上,隐然其间的甚至会有一些优越感,如郁达夫写他为鲁迅的版权纠纷而专程跑去上海交涉,显然是帮鲁迅而不是受鲁迅帮。当然,这有违“施人慎勿念,受恩慎勿忘”的古训。不过,郁达夫是性情中人,才华横溢,清狂自大,本来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规规矩矩谦谦君子。
端木蕻良写鲁迅是无限景仰,而写萧红却是平等的态度,有很明显的悼亡体色彩,他晚年还写了几篇诗词悼念萧红,这背后有舆论压力太大的因素,他与萧红的结合,以及萧红的不幸早逝,物议颇多。
汪曾祺写沈从文的回忆文章有很多篇,而汪曾祺的全集也只不厚的八册,说明其写作产量并不高,可见师生二人的恩情之深,遗憾的是沈从文未能活到获诺贝尔文学奖,否则,汪曾祺写沈从文的文章肯定还要多得多。就我个人而言,认为沈从文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实至名归,于国于民也更有益。
汪曾祺与端木蕻良是单位同事兼好友,惺惺相惜,话说得很有分寸,而又极到位,他说端木蕻良写画家王梦白的文章好,可是我翻了几本端木蕻良的散文选,居然无一收有此篇。汪曾祺的眼光,在文学与绘画这个题材上,那是没什么可说的。也只有在悼念端木蕻良的文章里,汪曾祺一反自嘲的低调风格,借老舍的话,抬了自己一回,老舍说:“我在(北京)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他用直接引语引用老舍的话说到这儿,下面还有一句:“端木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这显然是怕的理由,但老舍先生怕汪曾祺的又是什么呢,汪曾祺先生涵养超众,没明说!六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读同时代人回忆他的文章比读他的正式传记要轻松有趣得多,而且,回忆文章往往文字更生动、更真实,这是因为,传记无论是自己写还是别人写,都不免一本正经、结构完整、穿靴戴帽,而回忆文章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可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写作者最感兴趣的内容。
出于阴差阳错的机缘,我这几年为出版社编选了三种汪曾祺的集子,先后写了五六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盘点一番,汪曾祺竟然是我为之写过文章最多的前辈作家,而有必要如实禀报读者的是,我接触阅读汪曾祺已经很晚,同时汪曾祺也并不是我对其作品用功最多的前辈作家,所以从不敢以汪曾祺研究专家自居,我也没有机会与汪老先生谋面。故而,我虽然曾一再用“青山多妩媚”来形容自己对汪曾祺的敬仰爱慕或欣赏,但自己明白差不多相当于雾里看花,实在是不敢说已经清楚了。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一些观感与印象写出来而已。
作为编选者,我自己对这套书里所收诸篇都是非常爱读的,能有机会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视为莫大的乐事,为了体例上的完整,将我所写的关于汪曾祺的浅陋文字附在我编的这一册的后面,这样,书里每位人物就都有了被评说的文字,至于狗尾续貂之讥,则非所计也。
2012年12月1日写于北京闲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