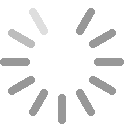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44792745
-
作者
余斌 著,杨苡 口述
-
出版社名称
译林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23-01-01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
-
书名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
定价
108.00
- 查看全部

内容简介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本书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
世纪回眸中,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中西”十年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民族危亡之际,自天津、上海、香港到昆明,西迁途中高唱《松花江上》,文明之火光焰不熄;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记忆里依旧是年轻的身影——初见“文学偶像”巴金,大轰炸后满头灰土的闻一多,手杖点在石板路上嘀嘀笃笃的吴宓,“夸我们是勇敢少女”的恩师沈从文,还有滇水之边的月下谈心,嘉陵江畔的重逢与告别……
学者余斌历时十年,用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
作者简介
杨苡,原名杨静如,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著有《青青者忆》(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编注)、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与杨宪益合集)等书。所译《呼啸山庄》系蕞流行的中译本之一。二〇一九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余斌,六〇后,南京人,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提前怀旧》《译林世界名著讲义》等书。
精彩书评
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
每次去看望杨苡先生,都能感受到她的安静,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冲击。她能够安安静静地激励别人、鼓舞别人。她是批判的,更是令人尊敬的,在她的家里,我无数次体会到那种来自杨苡的幸福。我相信,体会到这种幸福的绝不可能只有我一个。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 毕飞宇
本文属口述实录体,传主是已经百岁高龄的翻译家杨苡,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年龄、身份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其精神内核:这是一篇“祛魅”的好文,它破除了我们对所谓“zui后贵族”“簪缨之家”司空见惯的膜拜和讴歌。
——《读库》主编 张立宪
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西南联大》《九零后》导演 徐蓓
目录
第一章 家族旧事
发迹传说
大排行、小排行
父亲杨毓璋
母亲徐燕若
“妨父”之名
外面的世界
又一次大变故
天津搬家史
娘
大公主
二姐
亲爱的哥der
四姐和二姨太
“吾姐”和罗沛霖
姨太太们
八叔和四哥
老姨太与狗叔
大姑妈与四姑妈
姑姑杨丽川
来凤
潘爷
池太太
第二章 中西十年
“中国地”的中西
贵族学校
男老师与女老师
“初恋”
“真笨”
闯祸
乘着歌声的翅膀
“穷白俄”娄拜和美国人格莱姆斯
“重生”
立案与会考
三位语文老师
家政课与心理课
垦亲会
演话剧
从看电影到看中旅的话剧
唐若青
中西之外
苦闷
给巴金写信
“大李先生”
到昆明去
第三章 从联大到中大(上)
“云南号”
香港十日
闷罐车上
到昆明了
愉快的日子
青云街8号
沈从文先生
复学生
跑警报
我们的课
吴宓先生
女生宿舍
三人行
虚惊一场
联大的伙食
高原社
等待与误会
“颠三倒四派”
C.P.朋友
游行队伍里的陈蕴珍
母亲来昆明
绝交
“害毛毛”
结婚
玉龙堆
王碧岑、范梦兰
金碧医院
正字学校
大逸乐和南屏大戏院
岗头村
告别昆明
第四章 从联大到中大(下)
到了重庆
在丁家花园
在南开代课
哥嫂
做回了学生
新的生活
中大与联大
“高干子弟”
陈嘉先生
重逢
More than Friendship, Less than Love
换校长风波
两见“蒋校长”
顾诚之死
同学少年(一)陶琴薰
同学少年(二)陈琏
同学少年(三)巫宁坤、何如
同学少年(四)徐璋与王聿峰
同学少年(五)吴良凤
同学少年(六)许丽云和许丽霞
同学少年(七)马大任与文广莹
两地分居
柏溪
兼善中学
吕医生说的故事
日本人投降了
恶耗
复员
精彩书摘
发迹传说
外间说到我们家族的事,都会从杨殿邦开始。但那离得太久远,我听说的杨家发迹故事,都是从祖母说起。
祖母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叫吴述仙。吴棠在清河县做县令时,有位故交之子走水路送父亲的棺材回原籍下葬,从他那儿经过,他让仆役拿了三百两银子送去。谁知到河边码头上错了船,因恰好有另外一只灵船也在那儿歇脚,而且身份和吴的故交一样,也是道员。仆役回来报告,吴棠一听,知道是送错了。已经送出去,没有讨回来的理,他只好又拿了一份银子送上。他去故交灵船上致祭,顺道也上了前面仆役误上的那条船祭拜一番,船上的人自然千恩万谢的。这回将错就错,算是给他后来飞黄腾达埋下伏笔了:船上的人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那时候慈禧还没被选进宫里,等到掌权了,对当年落难时吴棠的仗义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
吴棠怎么会把女儿嫁给杨家,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吴家受慈禧眷顾,杨家就跟着沾光,这门亲事对后来的杨家,非同小可。有人说,这事儿是编的,我也不知真假,家里都这么传。另一件事应该靠谱一点,是关于祖母的死。说八国联军要进京的消息传来,全家惊慌,那时有各种可怕的传闻。祖母吓得不轻,听到外人传话,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从此一病不起,年纪不大就死了。
照家里传的这个,祖母似乎很胆小,外间传的都是“正能量”的,说她成了杨家的长嫂后如何和祖父一起带领弟弟们发奋读书,结果兄弟五个(我祖父兄弟八个,有两个早夭)参加科举考试,四个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杨家对吴家当然是很感恩的,我姑妈跟我说,父亲那一辈字里都有个“川”字(父亲杨毓璋字“霁川”,七叔字“朗川”,姑妈叫“杨丽川”),就跟吴棠做四川总督有关。
祖父杨士燮是长子,虽也中了进士,做过杭州知府、淮阴知府之类的官,但论做官,比不了先人,因为杨殿邦是做到漕运总督的。也比不了同辈,他的两个弟弟杨士骧、杨士琦,一个做到直隶总督,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说是袁的“智囊”),权势熏天。他也不大喜欢做官,官场没意思,官场黑暗看透了,杨宪益在自传里说祖父自号“三湖(壶)太守”,三壶是烟壶、酒壶、尿壶,总之是有点玩世不恭。
他曾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务,做过横滨总领事官,和当时的官员比是开了眼界的,杨士骧、杨士琦算起来又是洋务派的人,所以有点洋派。他在天津租界里买地盖房,儿子也都送出去留学。父亲和三叔留日,五叔七叔留美,八叔留法……除了老姨太生的两个,差不多都送出去留学了。
我对祖父的全部印象就是全家福的照片,还有他的画像。画像,当时称作“影像”。那时已经有摄影这回事了,我手头也还有祖父的“全家福”,但没见过单独的相片,只见过他的影像。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那时小有名气,没后来那么大名气,给人画像也是糊口,不是太贵,也不那么稀奇。影像很大,我想要比单元房的一扇门还大,到祭祖时就挂出来,前面摆上供品。影像上的祖父八字胡,穿布衣,不戴官帽,像《十五贯》里微服私访的况钟那种样子。并排挂的是祖母的影像,凤冠霞帔,很正式的朝廷命妇的装扮,和祖父的像在一起,一个随便,一个很正式,真有意思。
祖父祖母之外,旁边还有一位,影像小一些,一起受祭拜,应该是祖父的继室吧。这是我推断的,因祖母死得早。不可能是姨太太,祭祖时,若是有哪位姨太太已过世,也绝不可能在祭拜之列的。祖父有一个妾,后来我们称作“老姨太”。
前言/序言
【后记】
书成漫记(节选)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于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的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京师范学院(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他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齐如山的《北平怀旧》《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