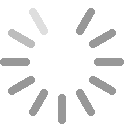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301284285
-
出版社名称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7-07-01
-
作者
[英]玛丽亚·阿里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 著
-
开本
其他
-
包装
简装
-
书名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
-
定价
59.00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语言富有哲理与诗性,不仅优美且见解独到。
本书前十章都是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内容丰富。
本书基于大量文本资料,探讨了文学与法律的关系,生命与永恒的价值。
内容简介
“法律与文学”的学科交叉研究被认为是近三十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跨学科理论研究。《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从实践中一起凶杀谜案入手,分别从“起源的神话与神话的起源:超yue俄狄浦斯之旅”“作为妇女再造词语的剧院:朝向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的肉体之胜利”“《以牙还牙》中死亡与欲望的婚姻”“差异前后的世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感观世界的法律:加缪的《局外人》”等文学作品中探讨法律和文化的关系。
作者简介
玛丽亚·阿里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剑桥大学法学硕士,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主要著作有《法律、精神分析与社会:认真对待无意识》(Law, Psychoanalysis, Society: Taking the Unconscious seriously)等。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法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实践、法学与文学、法学与电影以及法学与音乐等领域。
精彩书评
本书开创了法律文学批评研究的新时代,是一本系统性地、深入浅出地也是寓教于乐地研究法律中文学形式的著作。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此书,并极力推荐在法律和文学的教学课堂上使用此书。我建议首先从最后一章即“重新开始”读起,不仅因为这一章文字优美、荡气回肠,而且因为这一章是整本书之所以行之有效的开篇序言。
——彼得·古德里奇,纽约叶史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法学教授
(Peter Goodrich, Professor of Law, Cardozo School of Law, Yeshiva University, New York)
本书论述详实,文字激昂,在法律文学研究领域实属翘楚。纵览全书,行文高雅流畅,见解独到鲜明,论证强劲有力,洞幽烛远,辞微旨远,真知灼见遍布字里行间。我深信此书将会吸引世界各地读者的眼球而且将影响深远。
——迈克尔·弗里曼,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格兰法教授
(Michael Freeman, Professor of English Law,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目录
第一章 开端……虚构现实,一个短篇谋杀迷案
第二章 起源的神话和神话的起源:超越俄狄浦斯之旅
第三章 剧院里女人重演人世间: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的血肉之躯走向胜利
第四章 《一报还一报》中死亡与欲望之间的婚姻
第五章 差异之前的世界与超越差异的世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第六章 感官世界中的法制:论加缪的《局外人》
第七章 女性作为立法人的奇幻小说:安吉拉·卡特的《血室》是赋权还是诱捕
第八章 逃过火灾的档案热:《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法律记忆以及其他文本记忆
第九章 托尼·莫里森《宠儿》的语言、道德和想象力
第十章 “努力梦想”:博尔赫斯小说中女神的梦想
第十一章 重新开始:身陷迷宫的律师以及“从她走向永恒”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开端……虚构现实,一个短篇谋杀迷案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虚构主导的世界——大宗销售,广告,像做广告一样做出来的政治,电视荧屏造就的对经验世界任何最初回应的抢先占有。我们生活在一个鸿篇巨制的小说里。如今,作家已经越来越少需要创造其小说中虚构的内容。虚构早已存在。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创造现实。
——巴拉德(J. G. Ballard)《撞车》(Crash)
第一节 叙述性回避、奇幻小说与等级制度
法律和文学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或者,按照拉康(Lacan)的说法,“真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什么是法律和文学可以想象出来的地位?然而,我们赞同法律和文学不同,法律是处理生与死这个物质世界里的东西,法律和文学二者首先都是书面的符号。法律世界和文学世界都是词语的定义和存在所建构起来的,并且依附于后者。就是这些词语创造了不同的虚构的世界,而这些世界看起来又是那么不可避免。
任何企图通过法律或者文学的符号和语言来管理世界,企图俘获、驯化和统治这个如迷宫般复杂的世界都是枉费心机,这个世界的起源、设计及其设计者,我们都无从知晓。法律和文学都是人为的构念、人为的概念或者人为的抽象化,如同时间或身份一样,它们意在从混乱中创造出秩序,特别是律法方面,意在强加自以为是的秩序:对于当事人的身体乃至其灵魂深处进行书写,以便实现且取代他们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这个书写过程中,这些企图成为他们自己的迷宫,不仅对于那些想要闯入该迷宫的人,同时对于他们本人而言都是迷惑难解却又明心益智。
然而,艺术家承认甚至有时候就是要吸引大家去关注其构造物的偶然性和人造性,可是律法语言却要竭力掩饰其人造痕迹。虽然艺术家坦白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任意的、不完整的、假定的和临时的,但是律师却坚持假装他们是自然的、必然的,坚持认为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所有答案而且能够提供所有正确答案。因为他们渴望信奉原始点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开端、中端和终端这三端的,这个世界的运行有规可循,清晰可辨,并且结果也是可预见的,对此他们深信不疑,如同这个世界本身是不可知的一样都牢不可破。
我们对过去的无知、对现在的不解以及对将来的担心,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促使我们无论是作为法律和文学的作者还是读者努力认识并进而掌控我们的世界。所有这些阅读和写作都是在欲望中发生,在我们对他人以及他人欲望所产生的欲望中发生,拉康的镜子赋予我们充实感并且帮助我们夺回我们丢失的丰富童年。故事在这样的寻求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通过故事我们试图回忆过去,应对当下并展望未来,我们创造故事来掩盖我们所不了解的和无法接受的东西。对叙述的渴望,对开端、中端和终端的渴望,就是对于我们那不堪一击的身份的自我识别和确认。法律和文学的写作以及阅读给这个缺乏根基的世界临时提供了已被锚定的幻觉。然而,真相、统一以及终止只会带来自我的解体,带来只有死亡才会有的最终结局。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称赞叙述和悲剧特别具有净化的能力,因而能够抚慰听众和观众心中的恐惧和悲哀。叙述是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渴望叙述不仅对于悲剧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所有叙事作品同样重要,无论这些叙事作品是法律的、文学的还是法律文学的。有关法律起源及终止的那些理论,有关正义、自由、权利、判决以及解释的那些理论,它们共同参与管理我们世界的企图,企图将潜在的混乱缩减至可控范围之内。想要在我们的信仰、词句以及行动中发现意义的企图似乎没完没了,这些企图反映了我们妄想找到一个根基,一个超验的能指去对抗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观念、理论和神话在这个方面有着特别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类的成果(或许如同我在最后一章所提出的它们是男性的),渴望秩序和共性,渴望起源和目的,减少混乱和异质,减少对于已知的差异,最后达到天下大同。
不过,没有哪个叙述是完整的,总会有缺口、沉默和无知。叙述看起来解决了矛盾,而矛盾的存在又第一时间导致了叙述的必要性。线性叙述似乎非得有个结论,当它们再给出答案时似乎就给出了新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总是早已预先假定的。叙述因此发明了而不是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世界。不论是法律的还是文学的还是就像我们这本书所探讨的法律与文学的,叙述不是中立的:它们在追究、揭示和创造意义,并且将意义合法化。
进一步来说,在我们文化中有些叙述相比其他叙述享有特权:诗歌从哲学中脱颖而出,伦理学从美学中脱颖而出,理性从情感中脱颖而出,法学从文学中脱颖而出。在法学教育中,关于法律的起源、功能和需求,法官和法律哲学家对此的叙述要比其他叙述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哲学,它声称最有资格告诉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荒唐的。在柏拉图(Plato)看来,外行对于社会的认识不足信,因为外行既没有才智也没有闲暇去判断对错。哲学否定了门外汉的知识,并以追求真理为名为社会等级的分化作辩护。小说、修辞以及文学都认为自己关乎文体和哲学,同时它们也都认为自己是追求永恒真理的独立学科,即便不能超越神学也是有别于神学的。反过来,哲学家是知识的“载体”而不是观点或信仰的“载体”,他的工作不是艺术家所做的事情,而是立法者所做的事情,是给人类的理性制定法律。
不过,企图把哲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维持它的优越话语地位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即便是哲学也无法奢望脱离语言。哲学自身的定义和存在是通过把自身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语言,特别是小说的、文学的和修辞的语言。哲学虽然声称是要宣告那些无可辩驳的真理,但是也只能通过忽视语言的本构性和隐喻性的本质来作此宣告。德里达(Derrida)对于哲学的基础主义的批判取代了哲学和文学的界限:那些想要写哲学论文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无法与哲学内容分开的;相反,文学文本以及文学评论作出了大量哲学式的假定,跟那些声称要做纯哲学式的写作一样多。德里达揭示了语言是如何使那些探求真理和存在的哲学家们分心甚至感到沮丧,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哲学、政治理论当然还有法律都是以与文学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哲学依赖语言意味着它不再比其他的语言形式优越,因而也不再声称是构成其他学科的基础。特别是在解构的和心理分析的诠释中,这个据说是纯粹的、自我参照的语言再次回来,不断指涉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和独立性。随之而散的还有法律和理性的专横,哲学家和立法者都无法挣脱修辞抑或文学:与所有作者一样,他们都是任由语言摆布,对语言我们既不拥有也未掌控。
我们区分各种不同的阅读、写作和学习,我们区分各种不同学科,这都是法律文学研究的灵感的一部分,我们的区分因而是文化上的而不是自然的,我们是在建构而不是在施舍。这样的区分由我们语言实践活动创造出来,与此同时也依靠我们的语言实践,并且作出这些区分的人认为自己对真理的表述比其他人的表述都要优越,所以这些区分是分层次的。这个研究赞同我们当下的怀疑,即我们对于任何一种试图发现“真理”的方法、故事、理论或者学科都不信任,这不仅是因为后者只不过是掩盖权力斗争的一种幻象,谁有权谁就界定我们所在的世界,人们对此钩心斗角。尼采(Nietzsche)重新回到审美体验,这不仅有启发性而且也很有价值,福柯(Foucault)对于人文科学的批判以及德里达对于哲学中基础主义的抨击都是重写了诗学与哲学由来已久的恩怨。柏拉图发起了这场争辩,对此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把诗人从他的理想王国中驱逐出境。不过,这场争辩的解决使哲学付出了代价。自柏拉图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热衷于为哲学开拓出单独的角色,即作为真理的仲裁者,他们使用与诗学相同的技艺,却对诗学技艺大肆诋毁,只为达到自身的目的。总之,法律一直以来早就是文学的,同时文学一直以来早就是法律的,对此我即将论述。
企图将哲学和法律从文学中区分开来,正如我这本书最后一章所指出的,就是企图将女性从法律迷宫中排挤出去:尼采诉诸美学并没有妨碍他宣称女性是真理的敌人。相反,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就是一代又一代男性哲学家的一位代表,他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努力去证实抽象的语言、理性和常识,藉此来抵抗女性游戏、引诱和欺骗的语言所带来的诱惑和祸害。因此,正如德里达所认为的,“把艺术、风格和真理的问题与女性的问题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
男性律师偏爱抽象的语言、理性和智力也是企图否定触觉的、身体的和感官的东西:据说他们是通过克服词语来抑制女性用身体繁殖的能力,然而实际上正相反,他们是通过模仿词语来抑制女性用身体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否定每个人的“第一个家、第一个身体、第一个爱”:母亲。
前言/序言
译者序
法,在西周金文中写为“灋”,《说文解字》中这样解析:“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乃神兽,“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凡廌之属,皆从廌。”由此可知,法之意义在于维持公平正义,其手段在于法器,如远古传说中的“廌”和“复仇女神”,也如当今现实社会中的“司法系统”等国家公权力机构。
法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是由“天赋神权”的神之法逐渐演变为“契约精神”的人之法。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天子们自诩为“天神之子”,代理天庭履行神授君权的天神之法,如西周开始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礼制,秦朝推崇的“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汉朝独尊的 “三纲五常” 的儒家法律思想,这些替天所行的“道”在宋明理学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存天理,灭人欲”。如此宗族礼教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跟这种天子法律代理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西方社会的人神共治,希腊神话中奥瑞斯提亚弑杀至亲遭复仇女神追究,直至雅典娜在战神山设立雅典娜法庭审判此案才得以平息,雅典娜法庭的成立标志着法律由神之法开始走向了人之法。从此,由自然法、神之法衍生出成文法、人定法,诸多法门正是为了“触不直者去之”,以期实现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趋善避恶”(that good is to be done and promoted,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托马斯·阿奎纳在论述自然法时指出,自然法建立在一些“首要原则”基础之上,“趋善避恶”是首当其冲的第一准则。
东西方社会在商品充分发达、交易频繁发生的同时逐渐滋生出契约精神,买卖合同的出现基本保障了交易的有序推进,此时,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交易合同的签订是法律发展史上继雅典娜法庭成立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独立于神的旨意,法律由保护神的旨意更多地倾向于保护人的意愿,于是法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这也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关于情、理、法之三角关系的困惑,苏格拉底之死是人之法开始独立于神之法的一个投名状。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意志且依靠国家公权力机构来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本质在于阶级性,在于一时一地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约束力,而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想象,想象不受时空的约束。如果说文学是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那么法律则是企图规范心猿意马的“紧箍咒”,然而,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欲望,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欲望,跟其他欲望相比,法律这种欲望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归约性以及时空性,法律是想要对欲望加以控制的欲望。
文学是作者通过语言文字表达作者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的语言艺术作品,按体裁分类,文学主要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等,文学与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学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语言的想象,想象是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
想象,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可以根据现有事物的表象进行加工创造,或者根据已经认识的事物规律进行合理的逻辑判断和预测。想象,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包括有意识的想象(如文学创作)和无意识的想象(如做梦)。想象是认清事实和发现真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从某种角度上说,事后证明为真实可信的想象即为真相。对于真相的认识和表述由于感知和想象的不同而表现不一,如盲人摸象,也如小镇居民对于圣地亚哥被杀当天天气的回忆。真相,是像一堵墙,还是像一根绳索?真相,是阳光明媚,还是细雨迷蒙?如果真相就是“大象”或“天气”,那么每个摸大象的人和每个回忆那桩凶杀案的人都认为自己认识的和表述的就是真相。认知的局限性和表述的片面性表明,人们自以为是的真相不过是假象,是虚妄。如果真相和真理果真存在,那么只有那个“阿莱夫”(the aleph)才能认识和映射出它们,因为“阿莱夫”虽小,可是却包含了整个宇宙。真相弥诺陶洛斯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弥诺陶洛斯真的被杀死了,那么帮助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的不仅是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线团,更是那个“阿莱夫”。
顾名思义,法律文学主要研究法律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法律。法律与文学两者都是借助语言来表达和理解人和事的问题,区别主要在于,文学中的那些人和事可以是虚构的,而法律中的那些人和事则通常确有发生,法律对于言行有一定的约束力,文学却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且能拓展意识的自由空间。法律文学通过认知能力特别是想象力告诉世人,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思想、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法律体系的基质、发展和升华。希腊神话中所叙述的复仇、审判和乱伦禁忌正是西方法律制度的缘起。法律体系通过公权力机构维持社会秩序,从而企图控制眼耳鼻舌口身的欲望,文学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明辨是非,引导心灵和意识去体验美学的享受。欲望本无善恶之分,可是欲望的满足不可以不择手段,个人或法人的欲望原则上需要受到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约,如果欲望在实现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的权益或者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欲望的主体则当受到法律和道义的惩罚。在司法实践和法理研究中,对欲望的研判不容小觑,如犯罪动机是量刑轻重的一个考量因素,犯罪心理学在犯罪动机和作案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探究对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和矫正罪犯有着一定的意义,这些当然也是法律文学描写和论述的一个主要内容。然而,法律所惩处的欲望只能是已经导致既成犯罪事实的显性欲望,腹诽罪的废除是法律的一大进步,法律文学通过对于文学作品中犯罪起因、情节和结果的描述不仅可以揭示显性欲望还可以揭示更多的隐性欲望。另一方面,如果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这反过来也可能会导致发生犯罪事实作为欲望的一种代偿式满足。法律意在通过理性来疏导和控制非理性的欲望,欲望和理性都是通过意识这个介质产生的,法律和理性对于欲望的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意识的参与才能产生作用。
意识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在介绍量子力学的时候声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客观世界很有可能并不存在!”这种观点是对“薛定谔的猫之思想实验”(Schrdingers cat thought experiment)以及物质波理论最直白的解释,即意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客观世界在意识作用之前处于一个叠加状态(superposition),如猫既死了又活着,而一旦意识参与进来,客观世界就处于坍缩状态(collapse),则猫要么死了要么活着,不可兼得。意识就是这样通过波函数坍缩来改变客观世界。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的物质波理论指出,一切物质(包括光和实物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由此可见,物质和精神都是波动的现象,区别在于波动的频率不同,眼耳鼻舌口身所感观到的,是物质现象,而心灵和意识所识别的则是心理现象。现象来源于意识,即念头,物质是意念累积的连续相。念头无处不在,念头遍法界虚空界。念头也无时不在,弥勒菩萨说,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认识所有呈现在时空世界里的现象,也就是认识人类自身投射时空里的观想行识。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早就断言,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回事,因为物质是个幻象,是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也就是常说的心有所念。意念之多变化之快,导致了对客观世界和事实真相的认识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正是这个不确定性才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对于人类而言,唯一可以确定的真理恐怕就是人类向死而生。于是阿波罗下达法令:“人啊,认识你自己吧!”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主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了西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法律思想、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及其表达方式,揭示出西方法律一直在为父权法律背书,女性是父权法律得以建立的牺牲品,也是维持同性交往社会关系的交易对象。《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不仅是一部揭示了女性在父权法律社会遭受压抑的“她史”(herstory),也是一部研究法律文学发展的鸿篇巨制。该论著研究语料丰富,包括西方经典戏剧和小说等文学著作、流行音乐、影视作品以及南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研究对象的时空跨度极大,从远古的希腊神话到当代的文学艺术,从欧洲到美洲。本书作者玛丽亚·阿里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是全英国开设“法律文学”(Law and Literature)这门课程的第一人。她认为法律,即父权法律,只会导致更多的谋杀—复仇—谋杀的循环,死亡才是它的唯一归宿,因为法律有意抑制了女性的法律主体地位,法律是走向法律它自己的旅途,人类的成长就是俄狄浦斯的回家之旅。于是,作者呼吁创造另一种语言即女性语言去书写另一种法律即女性法律,当女人不再映射男人所需的自我满足反而是女性自身欲望的时候,就更加迫切需要这种新法律即女性法律,当女人开始在黑夜为她自己书写的时候,也就是女性法律得以建立的开端,跟着她才能走向永恒。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全书共有十一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章,旨在揭示女性是父权法律制度这个迷宫建立的起因、女性是法律迷宫排挤和吞噬的对象,同性交往的父权社会害怕差异性、害怕模仿、害怕女人,为了维护同性社会交往的秩序、为了控制欲望、为了避免乱伦禁忌,法律应运而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反映了父权意志,是男人欠缺生育能力的一种代偿。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旨在揭示女性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抗争历程,女性在父权法律面前长期以来只是局外人,被迫保持沉默,充其量不过是法律制度的装扮物,“让法律迷宫蓬荜生辉的第一批尸体就是女人的尸体:一个惨遭杀害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和一个作为祭品而被牺牲掉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跟伊菲革涅亚们不同,安吉拉们不再甘心成为男人书写的对象,她要为自己书写,她要亲口讲述自己被人玷污的那个羞耻,她还原谅了作为父权法律帮凶的母亲。同样地,阿里阿德涅们勇闯法律迷宫,直视弥诺陶洛斯,这回害怕的却是弥诺陶洛斯,“卷缩进他的壳里,冷冰冰地,像只蜗牛”。 当安吉拉向巴亚多讲述她的她史的时候,弱者的名字便成了男人,“整个社会开始营救受伤的那一方:即悲痛欲绝的男人”。觉悟后的女人们“打碎了词语的脊梁”,用自己的书写和回视来反抗家长制和法律暴力,提醒法律尊重他异性,敦促法律还给女人所有的亏欠,因为“一个女人就是所有的男人”。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对于法律文学研究的参考价值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文学是法律的基石。西方传统法律思想在希腊神话中得到充分的论述,谋杀—复仇—正义声张是西方法律的因果循环,谋杀的动因在于满足行凶者自己的欲望,乱伦禁忌是建造法律迷宫的主要驱动力。
(2) 法律无法解决法律意欲解决的问题。法律控制欲望的企图在谋杀—复仇这个父权法律迷宫中难以得逞,法律本身也是欲望,是控制欲望的欲望,是男人对生育能力欲望的一种替代性表达方式,法律其实也是一种模仿,尽管它害怕模仿、差异性和女人,破解谋杀—复仇这个报应循环的出路在于另外的语言和另外的法律,特别是女性的语言和女性的法律,一种用“身体”和“感观”打碎了“词语的脊梁”之后所书写的爱的语言和法律。
(3) 女人的存在不能只为父权法律而正名,女人应该建立自己的法律。女人是父权法律的牺牲品、交易对象和帮凶,女人一开始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夏娃是从亚当身上一个肋骨造出来的,雅典娜是从她父亲宙斯头颅里出生的。母亲,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家、第一个身体、第一个爱”,然而母亲有时候实际上又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家长制和法律暴力的帮凶,在安吉拉无法“在自家庭院晾晒污迹斑斑的亚麻床单”从而玷污了维卡略家族的荣誉之后,最想活埋安吉拉的却是她的母亲。安吉拉的写作和阿里阿德涅的回视都是在挣脱父权法律的桎梏从而开始建立另类法律:她们建立的“不是法律而是爱,不是死亡而是永恒,不是责任而是美好事物”。
(4) 文学的幻想是法律的理性在认识世界时的必要补充。宇宙万物无外乎能量、信息和物质,波动定律认为,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波动的,万物不同,皆因频率不一。文学作品认识世界的观点和角度跟现代量子力学很接近:那个“阿莱夫”虽小却包含了整个宇宙,这个“阿莱夫”就是一粒小光子,就是量子;人人都想得到两毛五硬币“扎希尔”(the Zahir),因为在这个硬币的背后可以发现上帝,这就无须像《神秘奇迹》中死囚犯那样只有在临死前的祷告中才听见上帝的回答;虚构的特隆星球(Tlon)甚至会入侵地球;《圆形废墟》中主人公可以通过做梦“梦出了一个儿子”,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梦中的人”。地球与“扎希尔”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境由心转,相由心生。宇宙的真相就是那一念,就是幻想。
(5) 真相在立场和情绪面前已不重要。在发生了那桩事先张扬出去的凶杀案之后,小镇居民对当时天气的回忆都相互矛盾,那么,那些亲历者对于这场凶杀案的证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小镇居民争相讲述所谓的事实与其说在揭示真相倒不如说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看法和情绪,真相不可得,“凡有所相,皆为虚妄”。一念迷,念念迷;一念觉,念念觉。法律注重规范性,而文学注重解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法律讲究证据,文学讲究情理。法律迷宫里的真相就是弥诺陶洛斯,弥诺陶洛斯也许本就不存在,“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法律在詹姆斯一世看来“是规定道德品行和社会生活的规则,而不是诱捕良民的圈套:因此,法律必须根据法律意义而不是文字本义来解释”。
《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是法律、文学以及法律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笔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不断停下来查阅有关量子力学、佛学经典、犯罪心理学等有关认知、意识和世界观的前辈所思考的智慧结晶,深感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英文原著丰富的启智性的语言和思想,非常感谢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对这个中译本出版的支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家里的女人们给予我的爱,感谢父母任劳任怨照顾全家饮食起居,感谢妻子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分担和鼓励。此刻透过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直视月亮般的太阳,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那些写满凌乱词语的草稿撕碎扔掉陪女儿出去寻找一片蓝天,哪怕蓝天下的阳光强烈不可视,“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完作业陪我玩”,“宝贝,现在就可以”。
薛朝凤2017年1月1日于集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