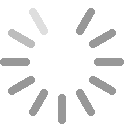-
已选 件

- 已售件
-
服务
- √7天无理由退货(拆封后不支持)
- √假一赔三
- √消费者保障服务



商品详情
-
ISBN编号
9787559844125
-
作者
李怀印
-
出版社名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22-02-01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是否是套装
否
-
书名
大学问·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
定价
89.00
- 查看全部


编辑推荐
李怀印老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是一本既能帮助读者将历史知识升华为历史认识,又能启发思考的好书。这本书有两点非常吸引人:一、作者对许多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零星的近现代史知识做了整合与重组,经过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宏观上解释了十七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二、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述,举例说来:李老师力图证明,不同于传统的屈辱史、失败史叙事,晚清近代化在许多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比如它避免了边疆的分离,政权建设也逐步近代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图书的装帧设计与图书内容非常契合。封面主要用了两幅图:《乾隆南巡图》苏州局部,反映东南财税对大一统国家的作用;《乾隆西征图》,反映西北边疆的平定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本版图。同时,正是东南充足的财税为西北用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撑。
1.中国近现代史知名学者李怀印新著,“超级教授”黄宗智主编的“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5号图书;
2.仲伟民、赵世瑜、陈锋、吴重庆、李里峰一致推荐,《亚洲研究学刊》《二十世纪中国》重点评介;
3.新见迭出。本书对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均有独到的见解;
4.研究方法新。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综合的视角努力挣脱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之泥潭,将诸多微观研究升华为宏观考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
5.视野宏大。本书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将近世中国的国家转型置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照察,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
6.时间跨度长。对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论述,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延续数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7.强烈的现实关怀。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求对今日中国历史认识具挑战性的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等深层问题;
8.史料丰富。充分利用大量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书中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图表作为支撑。
内容简介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精彩书评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从1640年代到1940年代),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li)、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党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共产党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
目录
第一章 导论/1
问题所在/1
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13
若干关键论题/20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42
边疆的整合/44
治理边疆/55
治理内地各省/62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76
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88
清代的战争与财政/90
清朝财政的低水平均衡/102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112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127
财权区域化/130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145
地方化集中主义/157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160
传统地缘秩序之终结/161
塞防与海防/164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与败/169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187
财政构造中的高度非均衡机制/189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陷阱/197
缔造新的民族/206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220
军阀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223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242
走向国家统一/252
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259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265
制造新的正统/269
党国之政治认同/279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292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299
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304
打造政治认同/310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320
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构造/327
一个比较分析/338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350
疆域的扩张与整合/351
王朝的衰落与调适/358
迈向民主抑或高度集权/364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368
“民族国家”的迷思/369
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372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376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379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384
参考文献/389
精彩书摘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
为什么东北如此重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度有所改善,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曾获得国民政府的津贴和补给;1939年以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摩擦加剧,但毕竟没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军队和敌后根据地由此迅速扩张。然而,共产党部队遭受了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以及后来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局部攻击。因此,通常情况下,共产党在战场上仍处于守势。对陕北和华北其他地区共产党部队来说,最为不利的条件是,这些地区均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支撑快速扩张的部队。正是因为陕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招募士兵,才迫使红军于1936年1月发起“东征”,进入山西(逄先知、金冲及2011,1:383)。出于同样原因,红军在1936年5月筹划西征,进入宁夏,以便接收从苏联获得的物资(同上:383,389,402)。后来,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控制的陕甘宁地区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导致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部队无法进入,打击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该地区的兵力为共产党的八倍以上(国民党25万人,共产党还不到3万人),一度使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总部陷入险境(同上,2:803)。正因如此,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随着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共领导人曾试图调整其军队和根据地扩张策略,优先考虑在相对繁荣的南方省份发展;1944年底和1945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接连发出指令,要求派遣共产党军队南下,在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新建或扩大根据地(TDGG,15:32—36,145—147,181—187)。
但是,1945年8月发生的几起意外事件——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及其随后在9月2日进入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使共产党战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极端重要性对中共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东北北邻苏联,西接蒙古,东接朝鲜——这些都是共产党国家或地区且对中共友好;一旦占领东北,中共部队将拥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根据地,而且,它从那里可以采取进攻性战略,对关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作战。其次,与中共已有的小而分散的根据地不同,东北地域辽阔,面积达约130万平方公里。当时面临两种可能,即既可能让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随即占领整个东北地区,同时也可以为中共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一旦遭到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能够后退,并在规划大规模攻势以最终从该地区驱逐和消灭国民党部队方面,拥有高度的机动性。第三,东北很富裕。该地区广袤而肥沃的土壤带来了农业高产,加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产生了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富余粮食,使东北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更重要的是,东北有发达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能源生产,占1940年代末全国重工业总产量的90%左右;这里的兵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此外,东北还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铁路里程达到14000公里,约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朱建华1987a:140)。一旦占据东北,这里将成为共产党部队向全国其他地区进攻的坚实后方。
对共产党而言,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控制东北,他们只好把作为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的华东地区作为争夺目标,但这样做胜算不大,因为这里驻扎有国民政府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依靠美国的慷慨支持,他们可以轻易地包围并击溃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力量。事实的确如此,国民党仅将约三分之一的部队集中在江苏和山东,便在1947下半年轻松地摧毁了共产党在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并将共产党军队逼退到山东南部,又在1947年5月进一步将其逼至山东中部。如果共产党军队以华北为优先进攻目标,他们将面临国民党从东北和华东的夹击。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先控制东北,利用该地区被苏方占领的优势,“封死”刚刚进入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并彻底消灭他们。只有在完全控制东北后,共产党的部队才能依赖东北充裕的军事和后勤供应,集中兵力在华东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叶剑英1982)。
由于指望从相邻的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从直至1946年4月仍然占领东北的苏联)获得实质性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很快放弃了原定的向南扩张战略,转而在1945年9月制定了新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LSQ,1:371—372)。毛泽东在调整这一战略时曾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考虑,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MWJ,3:410—411,426)七大后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向北发展”的战略。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要我能够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LSQ,1:372)
苏联的支援
尽管苏联有义务遵守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议,使中共不得不放弃其原有的“独占东北”计划,转而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不过,与苏联占领军的合作仍然是中共在那里立足并成功控制整个东北的关键(TDGG,15:433—436;金冲及2006:14—15)。1945年初,苏联军队欢迎共产党部队到达山海关,并允许他们接管当地政府的权力。后来,苏方允许东北各地的共产党军队自由行动,只要后者不使用中共部队的正式番号;在其进入东北的最初两个月,情形尤为如此(李运昌1988)。苏方慷慨提供的武器使共产党在东北被称为“抗联”的原有部队,能够在一个月内组建一支48500人的“自卫武装”。苏军还向曾克林麾下的共产党部队移交了原日本关东军离沈阳不远的一座军火库,使曾的部队能够从4000人扩大到6万人。10月初,苏方又通知中共东北当局,准备交给后者原关东军在东北的所有军事设备,这些武器足以装备数十万士兵。然而,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最初共产党军队实际上只能接收1万支步枪、3400挺机枪、100门大炮和2000万发子弹。10月下旬,苏军将在东北南部的所有武器和弹药库以及一些重型武器甚至飞机都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4月从东北撤军前,苏军进一步将在东北北部的日本武器移交给共产党军队,其中包括1万多挺机枪和100门大炮。据未经证实的资料统计,共产党从苏军手中接收的日本武器,总计约有70万支步枪、13000挺机枪、4000门炮、600辆坦克、2000辆军车、679个弹药库、800架飞机和一些炮艇(杨奎松1999:262;另有不同估计,见刘统2000)。因此,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力方面,共产党军队均在东北拥有绝对优势。1946年初,为了确保共产党军队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迅速占领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苏方以各种借口故意拖延撤军,并阻止国民党军队按计划进驻大连,接管城市(杜聿明1985:519—520,536—545)。
东北的实力
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三大战役的首役(辽沈战役)战场,共产党在此经过七个多星期的战斗,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并在1948年1月初占领了该地区。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东北成为中共最大和最重要的根据地。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以及高产的农业,这一地区很快便成为巨大供应基地,为中共提供人力、武器和后勤支持,使其得以赢得接下来的两大战役,即华东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和华北的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
东北首先是中共在内战期间最重要的兵源地。由于其积极招募且武器供应充足,当地的共产党部队迅速扩大,从1945年底的约20万人增加到一年后的38万人,到1947年底几乎翻番,达到70多万多人(朱建华1987b:602,604),占中共在全国新增兵力的一半;共产党部队在西北、华北、华东和中部省份的兵力,到1947年总共才增加30万人。到1948年8月辽沈战役打响前,中共在东北的兵力进一步增加到103万,远远超过只有约50万人的国民党军(王淼生1997:94)。它们不仅是共产党控制地区力量最大的一支,占整个中共军队的近37%,而且是装备最好的。从1945年到1948年7月,中共招募了120万名来自东北的士兵,占整个共军同期新增士兵的60%以上(朱建华1987a:286)。在辽沈战役获胜后,东北地区派出一支80多万人的部队,加上15万名提供后勤的民工到关内,构成了平津战役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朱建华1987b:69)。
同样重要的是东北的军火生产及其对关内作战所起的支持作用。1945年之前,在与国民党和日本军队打游击战时,共产党部队很少或没有使用重武器;相形之下,中共部队在内战期间的三大战役,采取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形式,每场战役涉及数百万兵力部署,密集使用炮火,消耗大量弹药。苏联移交的原日本关东军武器只能部分满足中共部队在东北战场的需求。因此,共产党军队在进入和占领东北后,利用现有设备和仍在服务的日本技术人员,迅速恢复并扩大武器生产。到1948年夏,已拥有55个不同规模的军工厂,每年生产约1700万颗子弹、150万枚手榴弹、50万枚炮弹和2000门60毫米大炮(黄瑶等1993:436)。1949年,其能力进一步提高到每年生产230万发炮弹,217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火炮,并雇用了43000多名工人(朱建华1987b:70)。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弹药对共产党军队在关内打败国民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东北通过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为中共在关内的作战做出了贡献。在1948和1949年,东北的农业产量介于每垧(约一公顷)900到1000公斤之间,每年合计生产1200到1300万吨粮食(朱建华1987b:141—143),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年征农业税共计230万至240万吨(1947年税率为21%,1948和1949年为18%)(同上:446)。在1946至1949年整个内战时期,从东北征收的公粮达686万吨;此外,还从农民手中征购了180万吨粮食和7488吨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农产品(DBCJ:210)。中共向苏联大量出口这些产品,以购买苏方的工业、医疗和军事物资。来自农业税和其他渠道的财政收入使得东北共产党政权在1949年可以支出相当于380万吨粮食的军费,其中45%用于关内各省的部队。此外,东北当局为关内提供了超过300万吨的货物,包括80万吨粮食、20万吨钢铁及150万立方的木材(朱建华1987a:384;1987b:71)。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宋平明(第一、十、十一章)
林盼(第二、三章)
翟洪峰(第四、五章)
马德坤(第六章)
董丽琼(第七章)
李铁强(第八、九章)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李怀印
2020年8月25日于奥斯汀